米歐敏、羅丹寧教授演講「晚明文人昆蟲學——以譚貞默 (1590–1665) 的《譚子雕蟲》為例」紀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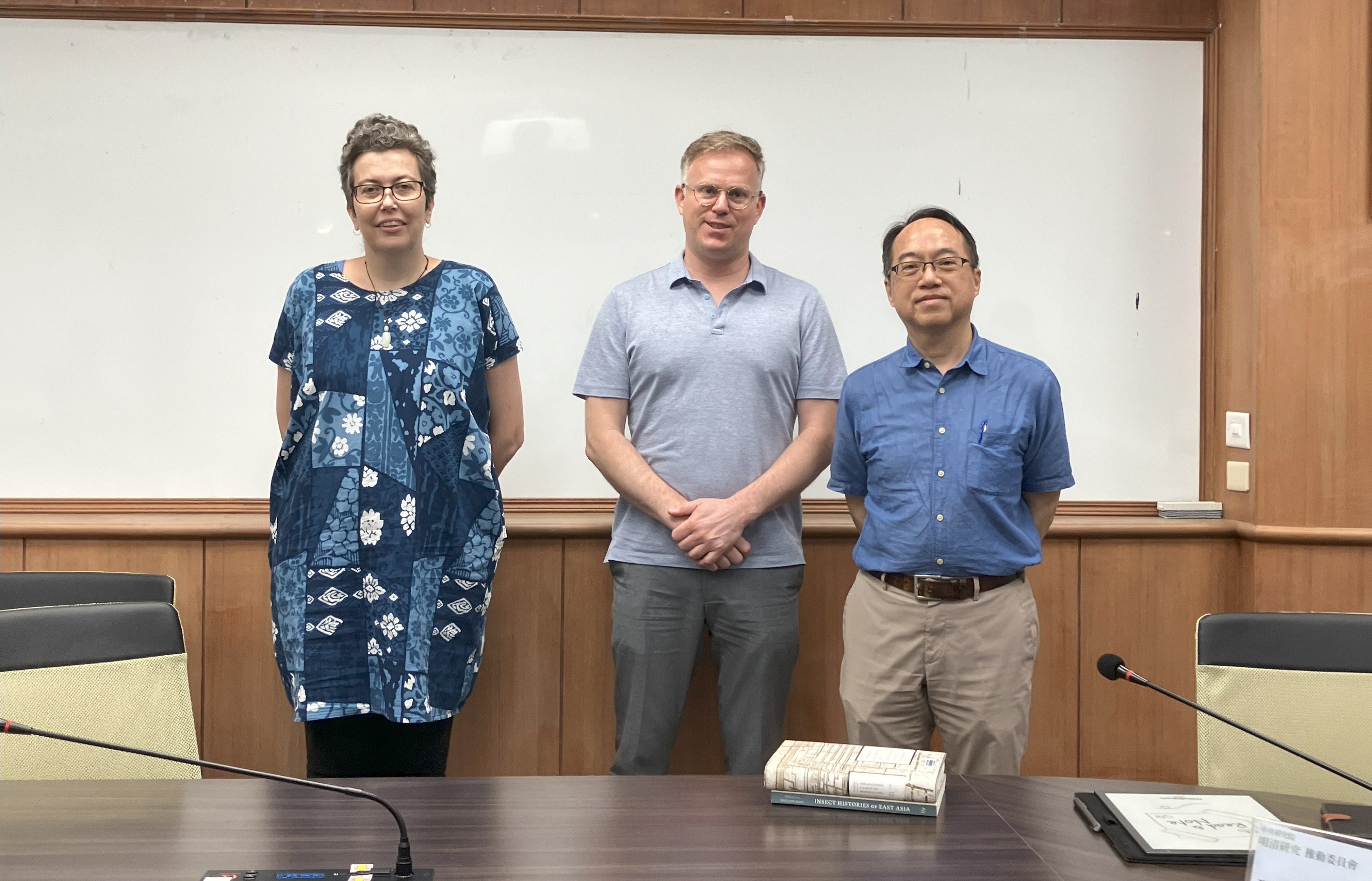
|
米歐敏教授現任職香港大學中文系,研究領域為周代吳國與越國的歷史和文化,中國古代文學中關於後宮的文言小説,以及中國先秦與漢唐時期的邊緣人群。重要著述包括《越國的榮耀:越絕書譯》(2010)、《懷古:古代吳國的文化遺跡》(2013)、《中華帝國早期的城市化:蘇州的地方志》(2015)、《晏子春秋譯注》(2016)、《椒房中的皇后:趙飛燕在中國文學和歷史上的位置》(2021) 和《新列國志譯注》(2022) 等。
羅丹寧教授於 2016 年取得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學位,現任溫州肯恩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助理教授。羅教授的博士論文以蘇州彭氏家族的信仰為對象,並持續對東亞動物史、環境史和醫學史有著長期的研究興趣。羅教授執編《亞洲醫學:國際傳統醫學研究協會雜誌》,並曾在《道教:宗教、歷史與社會》、《歐洲針灸協會雜誌》 《中國研究》、《生物學史期刊、《宗教與暴力期刊》、《韓國科學史期刊》和《東方報》等刊物發表論文。
首先,羅教授介紹他與 David A. Bello 教授合編《東亞的昆蟲史》(Insect Histories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3) 專書。該書嘗試從現代昆蟲學/生物學的認知視角,探討中國、日本、韓國歷代文人如何藉由文化傳統的文獻與思維,來分類、識別,乃至誤解昆蟲。羅教授提到,最早從人文學角度對昆蟲進行研究的學者,是加州大學的薛愛華教授 (Edward Hetzel Schafer, 1913-1991),可謂「中華小蟲學先鋒者」。薛愛華在〈唐代的螢火蟲〉(T'ang Fireflies) 這篇文章中,藉由對唐朝詩文的細讀,對昆蟲進行了專題的討論。羅教授說,他們的人文昆蟲學研究,正可謂接續薛愛華對於動植物的觀察與探索而來。此次的演講,乃是開啟新領域的嘗試,自謙兩人今天演講的目的,除了發表目前階段性的成果外,更希望通過各方學者的提問及討論,激盪出靈感與方向。羅教授接著介紹人類學者 Jeannie N. Shinozuka 撰作《生物邊界:跨太平洋植物和昆蟲遷徙以及美國反亞裔種族主義的興起》(Biotic Borders:Transpacific Plant and Insect 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Anti-Asian Racism in America, 1890-1950),指出此書藉由跨太平洋植物與昆蟲的觀察,進一步反思美國跨種族主義的問題,拓展微小昆蟲人文研究的意義。
羅教授強調,「蟲」字在中國文學的傳統語脈中,具有多元指涉性,與現代生物學談的「昆蟲」,並不能全然對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人對於「昆蟲萬物」,已有紛繁多彩的觀察。以先秦文獻為例,《禮記.月令》中就多次提及昆蟲,譬如蟲螟、蟲鱗、蟲羽、蟄蟲、孩蟲、蝗蟲、介蟲等,顯現人文傳統對於昆蟲的認知與互動情況。在《莊子.雜篇.庚桑楚》中,也曾提出「唯蟲能蟲,唯蟲能天」的說法,不只彰顯對於生態環境的觀察,亦賦予昆蟲思想文化上的意義。他進而以《二十四孝》中著名的「吳猛飽蚊」故事,指出人類如何利用蚊子展現孝行,並強調這個故事若從生物學的角度出發,並不盡然合理。傳統文人對於昆蟲雖有大致的瞭解,然而他們的記述時常有所偏誤。關鍵並不在於文人對昆蟲認識的不足,而在於對生物學和傳統道德觀的目的,大相逕庭。
米教授接續羅教授的討論,說明自己開始對人文昆蟲學的研究感興趣,與在韓國旅居時,受首爾蚊蟲困擾的生活經驗有關。她強調,蚊蟲雖是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生物,然而傳統文獻和文化,卻深深地影響人們對於昆蟲的思考方式。以蚊子為例,在先秦兩漢文獻中,就已出現不少關於蚊子的記載。如《荀子.解蔽》、《列子.說符》、揚雄 (B.C. 53-18)《法言.淵騫》等都有與蚊子相關的譬喻。而晉人傅巽所撰〈蚊賦〉,則是最早關乎蚊子的賦作。文末述及「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顯示窮人必須在蚊子的攻擊下生活、工作,反映出社會不平等的情況。
隨後,米教授的研究主題,從蚊子轉向中國文學中的蜜蜂。她指出,宋代以前的作品〈陰陽變化錄〉,就有「蜂有相,蜂有將。蜂蜂王,大如小指,無王則群死」之觀察,顯示人們已注意到「工蜂」與「蜂王」等生物學問題。當然,從昆蟲學的角度出發,〈陰陽變化錄〉的記載並不準確,然而作者藉由蜜蜂的生態特徵,描繪人類父權社會下,「所有成人都是雄性」的現象。這種以蜂群類比人類社會的觀點,亦可見於邵寶 (1440-1523)〈蜂塚嘆〉「一蜂亡,眾蜂死」、「一蜂君,眾蜂臣」的描寫,即以蜂群群聚的生物現象,類比人類的忠誠。米教授還注意到,明代女性亦大量書寫昆蟲。如沈彩 (1752-?)〈答鄰妹〉即以「蜜蜂釀蜜」來比喻讀書,其中「讀書徒自苦」的看法,實與佛教的傳統典故息息相關。沈彩進而以蜜蜂為譬,強調女性意欲創造屬於自己作品,並期許來生能再為女性(「來生仍老姥」)。米教授認為,文人常透過描繪昆蟲,表達對性別問題的擔憂;這種將昆蟲「性別化」的情況,相當值得關注。
綜上可知,傳統文人對於昆蟲的描寫,深受歷代文獻與文化的影響。從這個角度切入譚貞默 (1590-1665)《譚子雕蟲》一書,更可把握晚明文人昆蟲學的意義。米教授認為,譚貞默書寫的昆蟲賦作,並不容易理解,必須同時考慮賦/傳之間的關係,並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典故。米教授聚焦討論〈蠶賦〉、〈蟻賦〉、〈蝗賦〉、〈蚯蚓賦〉等作品,並指出譚氏對於荀子 (B.C. 315-236)〈蠶賦〉、《大戴禮記》、《韓非子》、《晏子春秋》、《列子》等紛繁典故的援用。她又以〈蟋蟀賦〉為例,指出文中提及鬥蟋蟀的遊戲,並引述《後漢書》「岑牟單絞」的典故,藉由戰事的描寫,勾勒蟋蟀好鬥的物種生態。再以〈蚯蚓賦〉為例,指出作者不斷引用音樂典故,描繪蚯蚓,藉此凸顯出家鄉「嘉興」的地方性色彩。
在演講最後,羅丹寧教授提醒讀者,要從《譚子雕蟲》書籍刊刻的背景脈絡,來認識此書。根據譚貞默自序,《譚子雕蟲》完成於崇禎 (1611-1644) 壬午年 (1642),已近明亡之時。在序中,作者提示撰作動機,實受到《莊子》、譚峭(字景升)《化書》、荀子〈蠶賦〉之影響。其中,譚峭為五代時的著名道士,而譚貞默認為譚峭是自己的遠祖。除了道教背景外,譚貞默亦曾撰作明代高僧憨山德清 (1546-1623) 之年譜,顯現此書可能具有不同的思想淵源。陳子龍 (1608-1647) 在〈譚子雕蟲序〉中,有意將譚氏的昆蟲和聖人之學連結。而錢謙益 (1582-1664) 讀畢《譚子雕蟲》後,也寫下十二首昆蟲詩,作為回應。從當時讀者的閱讀反響,可見《譚子雕蟲》的流傳情況,也有助於把握此書的出版脈絡。羅丹寧教授指出,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唯一的崇禎版《譚子雕蟲》,值得學界重視。
演講結束,與會學者與米教授、羅教授展開熱烈的討論。巫仁恕教授提出,明代蝗災盛行,此書的出現很有意義。其次,《譚子雕蟲》折射出晚明中國知識份子的考證學傾向,然其思路與清朝的考據學頗有不同。另外將《長物志》和《譚子雕蟲》類比,指出文人雖以「長物」和「雕蟲」命名著作,看似自謙,實則突顯出個人品味。楊正顯教授則提出,朱熹 (1130-1200)以降「格物」之學的認識理路,應促進文人對於「物」的研究視角,並建議考慮其他字書中關於昆蟲的記載狀況。丘文豪博士則提問,譚貞默的昆蟲書寫和其他的「物」的描述,有何不同?史語所訪問學者司馬蕾教授則就教中西昆蟲學的差異性與比較研究。蔡名哲博士則好奇《本草綱目》以及明代醫學知識,對晚明文人的昆蟲學是否造成影響?晚明文人對於昆蟲的文學表現,是否因考證或觀察而有所突破?
羅教授回應指出,《譚子雕蟲》在李時珍 (1518-1593)《本草綱目》出版五十年後才付梓。譚貞默雖注意到《本草綱目》,然並未受到很大的影響。米教授則指出,譚貞默如大部分的明末文人一樣,即便書寫自然,仍離不開文化典故。因此,他們所看見的昆蟲,並非只是當下此刻的形貌,而更重在回應傳統與仿古,且具有特定的時空背景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