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秀芬教授演講「Human Placenta for Healings and Longevity in Ming China」紀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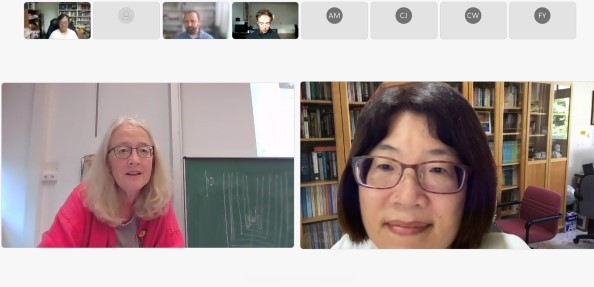
|
本場演講為中研院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臺德 (DE) 國際合作計畫「醫藥文化的物質性:介於歐洲與東亞之間」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講人陳秀芬教授表示,本次講題 “Human Placenta for Healings and Longevi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 可中譯為「療癒與長生:以明代的紫河車為例」。陳教授多年來關注中國傳統醫學「以人為藥」的觀念,本次她以風靡晚明社會卻也招致批評的「紫河車」為例,從其外型、性質、宗教及象徵等各層面,探討胎盤在藥物、食物與穢物三種物質性之間的轉換。另一方面,則呈現物質如何連結起晚明中國的煉丹、補養、醫藥文化,以及人們對於生育及死亡的想像。
細數本草典籍,可以看到「人藥」(human drug; human body parts as drug) 的範疇極為廣泛,包括頭髮、指甲、牙齒、髮鬚、陰毛、唾液、眼淚、汗水、血液、乳汁、精液等等,族繁不及備載。它們經常根據形體、特性或用途被賦予不同藥名。在明代醫典中,胎盤就有諸多名稱,如「人胞」、「胞/胞衣」、「胎衣」等較通俗之稱呼,以及「混沌衣」、「混元母」、「佛袈裟」與「紫河車」這類蘊含道教宇宙觀之詞彙;其中又以「紫河車」一稱最為人所知。在道教內丹 (inner alchemy) 身體觀中,「河車」為「真經之炁[「氣」之古字]」運載之具,加上《易經》與煉丹術理論的附會,明人——包括李時珍 (1518-1593) 等醫者在內——指出色澤呈紫之胎盤品質最佳。
紫河車的用法之主要推動者為「方士」和「醫者」,前者將其作為煉丹之材料,後者則認為胎盤可治「血氣羸瘦」、「婦人勞損」、翳病乃至於蠱毒。從唐代到明初,醫書上所記載的紫河車療效愈見增廣,除兼治女性與男性之虛勞耗損或體瘦骨枯、幼兒之癲癇或受驚,明代醫者吳求以胎盤為主方製成的「大造丸」,更宣稱能處理生育常見問題,如流產、難產、不孕,還強調有「助生子、包生男」之效,甚至在某些例子有起死回生之效。上述理論大致源於古代醫典認為胎盤為「人身之本元」、能補人身之血氣的構想。陳教授指出,對於晚明中國的士人、方士、大眾而言,胎盤既為藥物亦是補品,時而被視為救治危症、延年益壽之萬靈丹;究其為何大肆流行,仍與明代「養生」、「廣嗣」、「種子」概念之興盛有關。除了陳教授本人的養生研究,學者如費俠莉 (Charlotte Furth)、白馥蘭 (Francesca Bray) 對於晚明生育文化多有探討,可與紫河車的文化史相互對話。
接著,焦點由概念層次進入到物質層次。如何揀選、處理胎盤並炮製為藥,為修練者或醫治者須掌握的重要知識,而我們也可藉此看到論述的歧異,以及向現實妥協的理論微調。就性別而論,主張胎兒的性別應與服用者相同或相反之意見皆有,陳教授指出兩種見解,分別反映了「相似律」及「互補律」的巫術醫療思維。性別考量外,本草書普遍認為「首胎」之效用最佳,然而在十五、十六世紀,胎盤揀選的條件變得較為彈性,不少醫家強調只要母親的身體健康、肥壯,無論男女胎、無須首胎亦有良效。陳教授認為標準的放寬,或與特定性別且為首胎的胎盤取得困難有關。取得新鮮胎盤後,第一步往往是挑斷血脈並清除其血水和腥味。明代流傳的本草書,可見以「東流水」或「米泔水」洗滌的指引。炮製則有陰乾、蒸煮、火焙等作法,容器有砂罐、瓷罐、竹器、甑等。其中,酒蒸法似於晚明成為主流。
十六至十七世紀隨著食用需求攀升,紫河車的價格水漲船高,甚至孳生黑市、穩婆盜竊胞衣等現象,招致當時士人的批評。其中,福建官員謝肇淛 (1527-1624) 不僅譴責穩婆及富貴家族買賣胎盤的缺德行徑,也質疑胎盤的療效與該物本身的汙穢;醫者李時珍則批評食用人胞不僅違背自古「埋胞」之俗,以人食人、同類相啖更是野蠻如獸。陳教授指出,李時珍對食用胎盤的看法等同於他對使用其他人藥的憂慮——比起「不潔」,「不仁」才是問題所在。李時珍的論述反映了宋代以來新儒學的人道思維,而嘉靖朝 (1522-1566) 以降的士人也循此脈絡批判勢力坐大的道教方士。
經由上述內容,聽/讀者或已察覺,無論是胎盤的命名、處置手續、藥效乃至所招致的批評,都充滿了象徵意義及儀式性。實際上,反對紫河車補養之法最有力的理由,即為李時珍所提到的「埋胞」儀式。「埋胞」的紀錄最早見於馬王堆出土的漢墓帛書,其中記載埋藏胞衣應配合的時間與方位。西晉崔行功於著作《小兒方》中提出之「藏兒衣法」,更詳述了埋胞的日期、方位吉凶、適合容器、程序與忌諱等細節,成為後世參照之範本。儘管明代埋胞知識已大幅簡化,仍可見上述傳統的影響。「日用類書」是明人取得埋胞知識另一管道,如《三才圖會》以簡潔易懂的方位圖加上說明吉凶的文字。這些晚明出現的日用類書,一方面傳承了古代的生產禮俗,另一方面又將其簡化成常民易懂、易操作的形式。未止於明代,及至清末民初,埋胞儀式仍見於山東、江蘇、浙江、兩廣、福建及臺灣,只是方式與容器有所差異。
明代人們對於紫河車之拒斥,融括了對療效的質疑、對汙穢與禁忌的恐懼,還有道德焦慮。晚明醫者、士人強調胞衣不可食用,尚需慎重掩埋,才能庇佑嬰孩的健康與福祉,藉以反對紫河車補養之風,然其所據原理,卻同樣來自於「同類交感」之信仰 (sympathetic belief)。胎盤連結了胎兒與母體,作為孕育生命的容器,象徵生命之本元,故一方視之為補充生命的靈藥,另一方則顧忌不當處理對新生命所帶來的危險。陳教授認為,從「胎盤」(胞衣)到「紫河車」呈現了其由自然(生物)性質到象徵意義的疊加,而這個過程來自於人們的自身經驗、感知與想像。無論作為藥物、食物或穢物,嘗試理解其相關論述,皆有助於我們理解晚明對於人—非人、文明—野蠻 (civilised vs. barbarian)、物質—人體 (material vs. body) 以及性別與醫療之間的關係。
本場評論人為臺德計畫之德方主持人——布倫瑞克理工大學科學與藥學史系 Bettina Wahrig 教授。Prof. Wahrig 指出,本演講呈現了胎盤在儀式與醫療兩種場域的差異及相關性,以及不同脈絡下醫藥知識如何被再現,同時,以胎盤為例,更能展示性別關係與知識生產間的相互作用。
接著,Prof. Wahrig 試圖在歐洲醫療史中找尋有關胎盤的記載,發現中世紀歐洲也廣傳著使用胎盤所進行的儀式或醫療行為。此外,近代早期 (early modern) 歐洲醫學文本中以人為藥的例子,許多項目與陳教授在本草書裡發現的雷同,胎盤也出現在其中。差異在於,根據十七至十八世紀間以拉丁文寫成、轉譯為德文的文本,胎盤入藥的手續通常是洗淨、乾燥後研磨成粉,與其他藥物混合服用,以用於治療癭瘤 (goiter)、緩解春藥 (love-potions) 作用或助產。因此,Prof. Wahrig 認為前近代中國與歐洲身體觀、醫藥觀之間的親近性與差異性,具有繼續探索的潛力。
隨著 Prof. Wahrig 提出「人藥」思維跨域性的研究構想,同屬本計畫的成員紛紛提出可延伸探討之議題。中研院史語所張谷銘教授認為亞洲地區的印度及伊斯蘭醫學傳統,也可以納入討論或進行比較;專研阿拉伯地區與伊斯蘭醫藥史的 Dr. Ayman Atat 則補充奧斯曼 (Osmanlı) 醫學的例子。
另一個引起討論的議題是明代的特殊性,如 Dr. Dominik Medes 對於李時珍將食用胎盤與「野蠻」概念作連結很感興趣。陳教授解釋,人藥傳統淵遠流長,然而對胎盤/紫河車的態度轉變確實始於明代,尤其是批判論述的出現。李時珍不單反對食用紫河車,也對其他「人藥」(如經血)抱持懷疑態度,陳教授認為這些隱憂除了針對人藥本身,也隱含對當時帝王權貴著迷於煉丹長生之術而濫採人藥的批判。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呂紹理教授則指出紫河車的流行或與明代整體社會結構(如人口增長)有關,因此建議陳教授可將此研究延伸至人口更急遽上升的清代,比較相同的醫療傳統在不同時代與社會間的異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