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志史料讀書會」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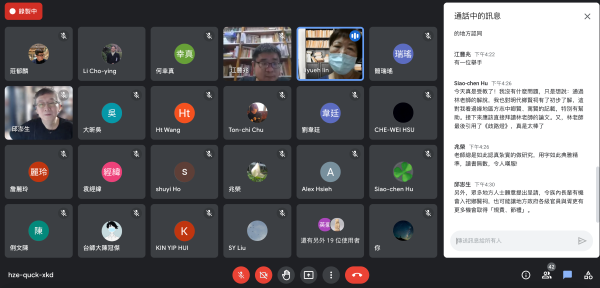
|
林麗月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專長為明史、明清社會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明代的國子監生》、《明末東林運動新探》、《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及〈晚明「崇奢」思想隅論〉、〈科場競爭與天下之「公」:明代科舉區域配額問題的一些考察〉、〈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等數十篇論文。本次講題為「鄉邦之光∕祖考之榮:明代鄉賢祠祀的社會文化史考察」,林教授延續 2009 年〈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的基層社會〉一文的關懷,集中討論以下問題:一、鄉賢祠祀的義理基礎,二、明代鄉賢祠祀的定制及其祀法,三、晚明鄉賢入祀的冒濫與整飭,四、崇祀鄉賢錄與明清家乘的增衍。
關於明代鄉賢祠祀,要從近世中國的廟學制談起。廟學制是由祭祀區域的「廟」與教學區域的「學」所構成的學校制度。宋元時期,地方雖有先賢祠、鄉賢祠、鄉先生祠,但仍未有全國統一的規制。當時所奉祀的先賢、鄉賢,主要是儒家學者且與當地有關的人物,而所謂「與當地有關」並不限定出生於該地的本鄉人,還包括曾在當地任官,或曾居住當地的先賢。到了明代,入祀鄉賢祠的具體資格限定於「生於其地」的鄉人,與「仕於其地」的名宦、「居於其地」的寓賢有所區隔,使得鄉賢祠與明清基層社會的關聯更為密切。
若論明代鄉賢祠的義理基礎,明代士人經常以文天祥年少時謁忠節祠,而有「不俎豆其間,非夫也」之歎的故事,以為文天祥能「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必是「祠之所感」,強調鄉賢祠祀可以感召鄉人,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徐一夔也曾強調,供奉於鄉賢祠者,因居於同鄉,或曾聽聞其「德行風節、文學事功、遺風餘烈」,或曾親見親聞,「至親且切」,遠較名宦更有在地性、親近性。在弘治《吳江志》及嘉靖《固始縣志》還錄有鄉賢畫像,更有如見其人、「近則易感」的作用。
鄉賢祠祀的請祀程序、入祀標準與資格審定皆有相關規定,我們可以藉由鄉賢祠逐漸制度化的過程,觀察時人所重視的「祀法」。一是入祀的準則,明儒莫旦 (1429-1510s) 曾引用先秦典籍中,「不祀非族」、「不當祠而祠者,謂之淫祠」之語,表達新昌縣鄉賢祠中有「他產」入祠(即非本鄉人入祀),並不恰當,其不合祀典等同於淫祠之祭。二是關於鄉賢請祀到入祀的程序。依據河南布政使萬衣(1518-1598,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人)的〈崇祀鄉賢公移〉可知,推舉鄉賢入祠,首先是由府州縣學生員公舉,當地鄉保具名,經府縣學的學官和生員呈文,報請知縣核實,接著由知府勘結,再送請提學御史覆勘。經過兩度覆勘後,由提學御史批准,府縣擇日奉入鄉賢祠。三是在資格審核的過程中,必須參酌「邑大夫士之公言」,以「考諸郡邑之誌」,即考索方志中的人物記載,可見地方志的生產機制與鄉賢祠的密切關係。四,鄉賢祠在廟學祀典中的位階。林教授以林希元 (1481-1565) 議論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1453-1508) 得祀鄉賢而未能從祀孔廟(雍正二年始獲從祀孔廟西廡)為例,指出林希元所論「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今祀鄉賢於學,即此意也。然祀之於學,則尤重矣。蓋凡有功於聖門者,始得從祀;不從祀而祀之學,其次也。」可見鄉賢祠在地方廟學祀典中的位階僅次於從祀文廟的「先儒」,在明清儒學下滲過程中具有重大意義。
明代中葉以後,鄉賢入祀的冒濫弊端日增,不少士人以入祠為辱。最為有名的案例是嘉靖年間江右王門學者羅洪先 (1504-1564),他認為吉水縣鄉賢祠所祀非類,入祀者俱是鄉里無賴,「恥其父與之同列」,因此將鄉賢祠中的父親牌位帶回家。文徵明 (1470-1559) 也曾告誡子孫:「吾死後若有人舉我進鄉賢祠,必當嚴拒絕之。這是要與孔夫子相見的,我沒這副厚面也。」鄉賢入祀的冒濫,正如董應舉 (1557-1639) 所說「古若晨星,今且踵屬」,前代鄉賢人數越來越少,當代人數則日漸增加。統計崇禎《吳縣志》亦反映這個現象,鄉賢崇祀主位共有三十三人,其中唐代一人、宋代二人、元代二人,明代有二十八人,又以嘉靖朝以後入祀者為最。
面對士人口中的「廟災」,朝廷方面仍有一些作為。嘉靖十三年 (1534),禮部題請〈嚴名宦鄉賢祀〉,令天下掌印官會同儒學師生,各查本處應祀名宦鄉賢,應遵照《大明一統志》所載,「逐一從公會議明白,備將職位姓名及履歷行實各相講明,務使事有考據,眾無私議,然後方許入祠」。萬曆初年 (1573),曾令各撫按官查勘各處鄉賢名宦祠有不應入祠者即行革黜,並要求提學官每年年終將所屬府州縣所舉鄉賢已准入祀者,「造冊二本,申送部科,以憑咨訪查考。如有濫舉市恩,不協公論,即指名參革。」另有提學御史力阻不應入祀者入祠,但冒濫之弊似仍不見有效遏止。清初宋犖 (1634-1713) 分析明清名宦與鄉賢之祀冒濫日滋,江南尤甚,而「江南之鄉賢祠則較名宦祠尤甚」。宋犖認為鄉賢大多是「子孫之陳乞」與「津要之請託」,較之名宦若無後人在世,士人「莫肯阿好」,鄉賢祠祀因此更易滋生弊端。
此外,林教授還注意到在明清時期逐漸增加的一種史料——崇祀錄。崇祀錄是由入祀鄉賢祠者的後代子孫為其出版,具有紀念意義的專集,同一時期相似的材料還有為節婦烈女刊刻的專集。就目前蒐集的資料來看,清代傳世的崇祀錄又較明代為多。崇祀錄有的以單行本流傳,有的與行狀、族譜等家族的史料合編,或以附錄收於書末。在明代文人文集中,則可以發現不少名人為崇祀錄寫序,如錢謙益〈書於廣文崇祀錄後〉、董其昌〈馬憲副崇祀錄序〉、陳龍正〈吳少卿海洲崇祀錄序〉等。此種文類對於明清家族史而言,應是可以進一步考掘的材料。
林教授過去研究明代國子監時,即認為傳統中國學校的歷史不應等同於教育史,而應視為社會史、文化史重要的一環。因此,討論明代廟學的鄉賢祠,自不能忽略背後的文化意義,及其與基層社會的密切關聯。本次演講主題取名為「鄉邦之光∕祖考之榮」,就前述鄉賢祠祀的討論來看,入祀者都是本鄉人,是本地足堪楷模者,當是鄉梓的光榮,所以是「鄉邦之光」。然而,對於入祀者的子孫來講,則是一種「祖考之榮」,更是生者的榮耀。
最後,林教授總結三個要點。首先,依據學者統計,明代的地方學校大約有一千五百所。朝廷普設學校並藉由廟學祠祀,府州縣學的學官與生員參與請祀公舉,成為國家旌表制度的一環,不僅擴大基層教化、促進地方認同,也彰顯了國家權力影響社會教化之深鉅。其次,明代鄉賢名宦請祀過程,除了鄉人公議以外,還需要檢索地方志所載的人物行跡。盛清時期,朝廷持續關注地方志重修,責成查核地方志人物傳記。由此可見,廟學祠祀、旌表制度的運作,與地方志人物傳記的生產關係非常密切,值得進一步注意。最後,崇祀錄的編纂涉及家族記憶的傳衍,對家族史與地方史研究來說都是值得深掘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