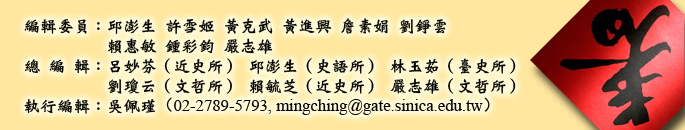專題報導:
中央研究院「2011 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1 Prospects of Ming-Qing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活動側記
(下篇,11 月 25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林佑儒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整理、撰稿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吳景傑、陳佩歆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 劉威志
協助採訪

主題演講二
鍾彩鈞:〈晚明關於人性的辯論〉(“The Debate on Human Na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這場演講由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焯然主持。鍾彩鈞教授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系博士,長期研究明代思想史。本講題比較顧憲成(號涇陽,1550-1612)和管志道(號東溟,1536-1608)對「性善論」和「無善無惡論」的辯論,及其與世教的聯繫。
在中國思想史上,「性善論」與「性無善無惡論」有其相近之處。自從王陽明提倡「四句教」以來,有關於無善無惡的論辯就成了明代中後期思想界的重要議題,主張性無善無惡者,又多持三教融合的立場。關於此課題的辯論,除了著名的四有四無、九諦九解之辯,更有顧涇陽與管東溟之辯,管東溟以佛教立場說明本體,兩人的辯論更將儒佛之爭推上檯面。管東溟主張性體無善無惡,認為善惡相對如同陰陽,而太極之中並無陰陽相對,故人性本體也沒有善惡之對。顧涇陽則主張性善論,認為性體是絕對之善,並非無善無惡。管東溟與顧涇陽皆同意善惡分判的依據在於天理人欲;顧涇陽主張善在天理之中,惡在人欲之私,不能以動靜有無為判,管東溟不僅區分天理與人欲,又以至善為理之靜,是道德實踐的基礎。而在世教的維持上,管東溟認為晚明儒教流於虛偽與假道學,故主張回歸程朱的道德規範以矯正儒家內部的危機。但顧涇陽認為管東溟的無善無惡說並不符合程朱學,亦有損於道德規範的建立。事實上,管東溟之論源於佛教義理,其無善無惡的心體觀對於維世善俗也有積極的作用,可以說是突破了傳統佛教的框架。
鍾教授認為,顧、管兩人深具博辯長才,又居理學思潮的後勁,因此在辯論和體系都更加完整。顧、管二人,都強調性為絕對本體,不與氣質相混,因此性體不能在經驗、相對的層次上立說,然兩人的思想仍有異。顧憲成的本體觀可以說是 「道德」的,而管志道的本體觀則是「超道德」的。
管志道雖然融合三教,且以佛教如來藏講心體,但他的學問旨在維持世教,對於當時走向極端的霸儒與霸禪進行批判。他是一位保守主義者,其思想特色是將程朱學注入佛教真性觀,並以規矩矯正放蕩的王學。
提問時有學者問道,管志道的生命觀到底是入世還是解脫出世?鍾教授認為佛教自然有入世的層面,但以解脫為目的,管氏讀佛教經典,於華嚴宗最為感動。佛教的教義本身是有「建教」的,但那是戒律。管氏與之有別,他的建教觀是「孔矩」而非佛教的戒律。
熊秉真教授也接著說,她在美國時曾遇到黃仁宇先生,黃先生跟她說,不懂佛理很難了解中國思想史,尤其五四以後,宗教學一直受到忽略。她想知道,這些明儒的佛學好不好?同時,也可否從明代的佛學立場看理學家?鍾教授認為,明代佛教原是衰弱的,然正如荒木見悟教授所言,是受陽明學影響而興發了明代佛學。管志道在荒木教授的分類上被歸類為宗教性較強的士大夫,其學術根柢是佛家,但個性是保守的儒者。
會中也有學者提到李贄與管、顧間的關係。鍾彩鈞說,管、顧二人是反泰州學派的,雖然後來沒再就人性議題辯論下去,但是他們之間有共識,都認為何心隱和李贄是霸儒。

場次四、明清文人研究
主持人:嚴志雄(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員)
發表人:
嚴志雄:〈錢謙益研究之反思〉
王鴻泰:〈明清士人的異性情緣與情色意識的發展〉
蔡長林:〈文章關乎經術——譚獻筆下的駢散之爭〉
「明清文人研究」此場次由當今多元而複雜的文人研究做為出發點,認為文人除了指涉某些特定人物外,文人作為一觀念也可以與階級、身分、經濟、價值觀、審美觀或生活實踐等層面結合,研究方法因而得用跨領域的方式處理。

嚴志雄教授〈錢謙益研究之反思〉一文表示,從乾隆皇帝等人對錢謙益發出嚴厲的批評後,對於錢謙益的思考一直無法擺脫歷史主義及道德主義的枷鎖,論述也陷於泛歷史和泛道德主義的術語中。嚴教授認為有必要回歸到文學本體論,即從文本的形式、目的、功能和結構等,來探索錢氏的精神、思想與情感。現今對於錢謙益的研究若想突破既有的泛歷史、泛道德主義的話語、心理形式,必須回歸到文學的本體論上重新思考錢謙益,透過文化形式與認知場域的視角,考慮其形象、身分、思想、行為等面向。循著錢謙益文本的形式、目的、功能、結構、意象、修辭、寓意等探討,可體會其性格、情感、內心底蘊,更可超越一般帶有目的論的歷史觀、泛歷史以及道德批判性的研究,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王鴻泰教授長期關注明清文人文化中的情色課題,〈明清士人的異性情緣與情色意識的發展〉一文以士人的生命史、情色內在意涵與社會文化脈絡的角度處理此一議題。王教授提出有趣的疑問:中國人有沒有青春期的認識?這篇文章利用醫學角度重新思考,如從《黃帝內經》看中國人的身心成長史,又透過禮教規範的社會體制來看社會對「成人」的定義。明清文人在不同的生命階段,透過接觸生活周遭的女性,有不同的情欲內容與情色意識的發展。年少時身邊的婢女就可能開啟其情色的想像,「弱冠」可能就有婚配。青少年以至婚配之後,家庭以外的社交生活中,妓女也會是其重要角色。這種情色文化反映在社會文化層面上,便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的創造活動。

蔡長林教授〈文章關乎經術——譚獻筆下的駢散之爭〉一文處理的是譚獻在駢文與散文之間所顯示的立場。從乾隆以來,為駢文爭平等,歷經以駢文為正宗的嘉道之際,到同光間的不分駢散,譚獻所主張的駢散不分在當代並不是一個孤立的論調,而是一種群體的作為。譚獻的特殊性在於主張,文章背後要寓載有風雅之思與聖人之道,而透過譚獻的學術立場觀察其對於文章的評斷,可見由於清代駢文與經生的密切關係,譚獻評論駢文褒多於貶,論及散文,則對桐城古文貶多於褒。

胡曉真教授講評時表示,明清文人研究是一個發展較為完備的研究範圍,無論事蹟、個體、群體的研究都十分豐富。「前瞻」所著眼是如何在已經累積的研究成果上,進一步立體化明清文人研究,尋求個人和群體間細密的聯繫,探索文人生活、心靈的多樣面向。過去明清研究中的「文人」多為廣義泛指,但此場次中所發表的三篇論文在相當程度上卻展現出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間的主客交融;在議題的選擇和學術文字的呈現上,研究者的主體聲音都清晰可聞。比如嚴志雄和錢謙益的文字之間, 可說相互交映。此外,本場次領域涵蓋古典文學、經學和史學,研究對象包括文人、群體和學者,展現出文人生命與文本的多樣面向,也提示著突破現代學術分割和分類邊界的必要 。三篇文章可謂分別表現出「文人之聲」、「文人之私」與「文人之文」。王鴻泰的研究範疇可說是文人之私,他突顯出傳統文人「也有」青春期,從比較現代性的眼光,深入文人的自我剖析。在這裡,明清文人的情色意識不是直接表述,而是藉家訓,學規,女教等形式,以否定方式體現文人對青春期的自我審視。蔡長林所處理的是文人之文,以文章為經術的核心,引申開來,可說文學史就是經學史甚或學術史。經學家也是文人,文學與人類都有內在聯繫,所以文字審美絕非學術的外圍,而是中心。就嚴志雄所研究的錢謙益而言,則表現出文人之聲。他的論文宛如「錢謙益研究宣言」,也像是在傳授閱讀明清之際文人的「教戰手冊」,文學與閱讀的政治脈絡交織,他提出的研究方式——從一章一句的組織、聲音讀起,這猶如聆聽音樂之細微起伏與沈默般解讀文人的方式,綿密而具穿透力。如此又可連結到上一場主題:「動亂時期的文人」,像是張大復雖然不是鼎革之際人,但卻擁有文人的騷動之心,因此動亂可以是廣義的概念,青春期不正是如此,錢謙益文字的多義不也連結其動亂的心靈底蘊嗎?
場次五、再探物質文化:由「我」觀物,由「物」觀我
主持人:邱澎生:(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發表人:
李焯然:〈知識與品味:從《朱砂魚譜》看明代江南的消閒文化〉
巫仁恕:〈消費與性別:明清士商的休閑消費與男性特質〉
熊秉真:〈所謂「物質性」的一些文化史思考——「蔘」、「蟋蟀」及其他〉
物質文化是明清研究近年來的重要發展議題,本場次「再探物質文化:由『我』觀物,由『物』觀我」的立意,是欲挑戰有關認識西方「消費社會」與「現代性」的單線發展史觀,進而勾勒明清中國社會文化變化的自身脈絡。

李焯然教授長期鑽研中國思想史,此次則將側重物質文化的相關議題,提交〈知識與品味:從《朱砂魚譜》看明代江南的消閒文化〉這篇論文,從明萬曆張醜的《朱砂魚譜》來探索明人對養魚知識和品種之要求。北宋時代開始,金魚的遠祖金鯽便已成為達官貴族用以消遣取樂的對象,透過人工養殖的方式,金鯽變化為人為培肓的金魚。明代的金魚從池養變為盆養,其色澤與體型也產生了較大的變化。《朱砂魚譜》對於金魚各類相關知識記載頗為詳盡,其中不僅反映明人消閒文化的品味走向,還呈顯類似某種數百年後有關進化論或優生學的知識。從某個角度看,晚明雖被視為一個玩物喪志的時代,但卻仍然可能蘊含著某類值得重視的科學知識。

巫仁恕教授受到英國工業革命研究有關性別消費觀的啟發,將討論視角放在明清中國。社會學家已經認識到消費行為與消費取向是建構社群認同的重要途徑與象徵,而消費行為的差異也反映出性別的區分,〈消費與性別:明清士商的休閑消費與男性特質〉一文探討明清士大夫如何批評當時婦女的消費行為,強調女性休閒活動對明清士大夫造成的某種焦慮感,進而挑戰了明清男性士大夫在消費領域的獨佔性。明清士大夫對女性消費與休閒行為的批判,不僅反映男性面對女性蓬勃發展消費行為的內心焦慮,又促使男性透過休閑旅遊與購物消費而重新調整了既有的男性消費文化,最後並發展成為明清士商階層共享的消費文化。

熊秉真教授一開始即強調「物質性」(Materiality) 在明清研究是一個鬆散且模糊的概念,學界對物質性研究也沒有足夠的重視。物質性對明清研究何以重要?熊教授由明清社會對「蔘」與「蟋蟀」的消費,闡述「物質性」研究視角的重要意義。〈所謂「物質性」的一些文化史思考——「蔘」、「蟋蟀」及其他〉一文首先藉由人蔘擁有的孝親意義來突顯出它的高級價值,接著從海外花旗蔘出現的現象,看法國傳教士如何推動人蔘貿易。人蔘從一個高價、特殊、輕便易攜的商品,進而成為明清社會短程與長程貿易的重要商品。熊教授接著提到蟋蟀除了給參與鬥蟋蟀者提供娛樂性之外,其實還進一步昇華為某種「無流血戰場」的符號表徵。透過時人培養蟋蟀時對大小、尺寸、壽命以及其他特徵的重視與論述,可以深入分析明清鬥蟋蟀行為背後的各種文化意義以及社會關係的相互連結。要之,「物質性」是一種以物為主角的特性,而物質卻未必一定要只限定在在明清中國的特定空間做討論,我們需要一併觀察同時期歐洲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相互關連,不能只侷限在中國、歐洲的特定空間,並應該與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建立跨學科的交流。

邱澎生先生於評論時指出,這三篇報告可以很好地反映明清研究具有前瞻性的四個面向。首先是近十餘年來的明清研究,原先偏向思想與文學「形而上」研究面向的學者,以及原本只重視經濟和環境研究的學者,雙方有愈來愈多的互動與交集,進而產生類似社會科學界「觀念論」和「物質論」兩種不同論述立場者更密集的互動,促成學者的相互啟發。二是有更多學者針對物質性、知識性或是人性的複雜關係,進行較集中的探討。以蟋蟀、金魚研究為例,人們在「玩物」之餘,進而探索相關知識是否以及如何反映當時人們對生物相關知識的重新界定;這些「物、物質」如何進入甚或是衝擊當時中國的知識體系?都已成為亟待探究的新課題。三是有更多研究試圖呈顯人情和物性的細緻關聯,並也留下一些可以繼續深入探究的課題。以人蔘為例,中國藉由人蔘或花旗蔘來盡孝道,這種物性與人情的互動模式是否與同樣食用人蔘的韓國有所差異?再如巫仁恕先生文章提到當時人們藉特殊物品牟利的所謂「好事」,是否也可被視為是另外一種不被認同的所謂「雅」的消費行為?同樣的物,卻反映不同的評價,其中似乎留有某些足以探討人情與物性互動的有趣線索。最後,明清中國曾經出現另類現代性的可能性如何?包含這場議程的三篇報告在內,明清消費文化研究呈現的雅俗共賞抑或是雅俗之分的緊張性,以及雅俗區分意義的逐漸「平民化、大眾化」,讓「平民的聲音」也逐漸浮現在明清消費文化裡,這些都是值得重視並有待繼續深化的研究議題。

場次六、清代臺灣經濟史的新議題
主持人:詹素娟(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發表人:
林玉茹、金衛東:〈林爽文事件前的臺灣邊區圖像:以乾隆 49 年的臺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
林文凱:〈清代與近代早期英國市場經濟的性質比較:以土地所有權體制為焦點的分析〉
曾品滄:〈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的生態環境與經濟〉
本場次「清代臺灣經濟史的新議題」由詹素娟教授主持,由地圖、經濟和環境來探索清帝國對邊區的開發,共同關懷清代臺灣的人與土地間之緊密關係。

林玉茹教授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金衛東教授合作,以最近出土的《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為探論中心。此圖呈顯各地番地界外的土地開墾、請禁等狀況,十分詳盡,較之現今藏於史語所的《清乾隆 25 年台灣番界圖》的史料價值不遑多讓。林、金兩位教授認為此圖便是乾隆 49 年繪製的《台灣番界紫圖》,可反映乾隆末期邊區的圖像。乾隆 15、25、49、55 年,清廷曾經四次釐清番界外土地,並繪成紅、藍、紫、綠四色之四張番界圖,其中紫線圖中附有四縣一廳的圖說,藉此可以考見乾隆末年的邊區圖像。乾隆中末葉,邊區出現漢番混耕的情況,甚至部分地區以熟番為拓墾主力,成為純番或熟番的優勢地域。紫線的畫定,也將大甲溪以北地區大半的平原地帶劃入界內,進入全面開墾狀態,部分地區甚至已經進逼淺山丘陵地。

林文凱教授反思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的理論,比較清代台灣和近代英國的土地所有權體制,並探索同一時期中西社會經濟性質的異同。對於 16 至 18 世紀中西經濟史,彭慕蘭以中西土地與勞動市場體制的比較為例,指出中西方在 19 世紀初工業革命前,皆經歷了亞當斯密式的市場經濟發展,而面對隨後出現的馬爾薩斯式的生態危機,英國以煤礦與新大陸的貿易、殖民解決了危機,並促成與東方經濟的分流。但是透過比較中西方在土地所有權體制之後,可以發現雙方同樣都經歷過土地所有制的變革,產生農業商品化,但其變革立基於不同的制度。英國奠基於近代國家的官僚、財稅、行政技術,並有近代法律確保。林文凱指出,中西都經歷了土地所有權的變化,然兩者制度不同,清代台灣的「一田二主制」奠基於傳統家產官僚制的原額行政與粗略的統治技術之上,雖有效促進農業商品化的發展,但不足以提供工業發展所需的完整制度基礎,需要靠傳統社會人群網絡建構的社會與民間維繫,因此農業也許可以商品化,但終究無法像同時期的英國,因具有近現代官僚體制、理性計算與法律而形成工業發展的制度基礎。

曾品滄教授發表〈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的生態環境與經濟〉一文,試圖以滿足島內市場為主要消費需求的養殖漁業為例,說明其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藉以證明除了外部(兩岸貿易、國際貿易)市場外,以島內市場為範圍的地方型產業自清代以來一直存在著相當的經濟活力,甚至還可能形成資本化的現象。作者比較盛行於台灣西部平原的「魚塘」和台灣西部沿海的「魚塭」兩種養殖漁業生產模式,來突顯商品化的發展軌跡。前者作為水稻栽培之副業,雖然隨著水田的擴展而散佈全臺,但也因為依附在水稻栽培下,水資源的利用受到限制,並得跨海從廣東等地取得魚苗,在多重限制下遲未能脫離副業形態。後者則是對於臺灣西部沿海不適合農耕之浮復地的最適化利用,也恰當地嵌入當地居民的消費生活秩序中,滿足府城居民對於鮮魚消費的需求,因此具備了專業化、商品化發展的條件。雖然獲利甚巨,但因成本高、風險大,成為府城富商重要的投資標的,從而在清中葉時逐漸形成資本化的現象。

李文良教授講評時提到,林玉茹的文章由「紫線圖」突顯清帝國統治臺灣時面臨的問題和政策轉變;此圖與其他版本的界線變化,也體現了清朝治臺的過程,把許多歷史脈絡連接起來。令人懷疑的是,此圖是否可以視為定案?同時,地圖是否真能代表政策的實踐?也許應該用更精準的事件來對應、比較?另外,劃界後,漢番仍在界外觀望,政府逐漸開墾,界線越劃越外面,所以劃界也是帝國領土擴張的象徵。林文凱的文章積極地讓台灣與中國、西方在經濟研究的層面上對話,這讓我們知道台灣的土地所有權原先有近於工業革命土地權益的概念,但在「一田二主」的土地買賣交易成本下,無法提供其工業發展的基礎。問題是,清代文獻中不太看得到「一田二主」的成本,這方面也許可再多加處理。曾品滄的文章關心的是鹹水漁塭的問題,包括發展資本化、專業化的行業,從而顯示臺灣本身也可發展出高度獨立與專業化的漁塭業。但這篇文章太注重漁塭業在臺灣西南方適應的問題,卻沒集中討論漁塭業在島內消費市場的重要性,也沒考慮到其他漁製產品在各地的交流。同時,曾品滄也提到生態環境,巴達為亞日記中記述,此地就是因為過度發展漁塭業而衰弱的,臺灣漁塭業是否對府城週邊有影響?
在這場討論中,以林玉茹的《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引起最多與會學者的討論。中研院社會所的柯志明對林文中把該圖做為完美句點表示懷疑,這張圖應該不是給乾隆皇帝的劃界定案,若真是定案,則令人感到可怕,因為成圖的時間太快,違反當時開墾者的利益。胡明輝也好奇這張圖的準確性。中研院臺史所的洪麗完表示,文中對於番界的敘述也得考慮到生番是否原先住在這裡,還是其中有越墾者。有些地方原先是熟番地,劃界下去變成界外。同時,地圖也可能和民間社會的認知有差異。林玉茹、金衛東最後回答道,此圖並非定案,福康安在乾隆 53 年的奏摺中也說明,朝廷未正式核定這方面的治臺政策。

圓桌發言
R. Kent Guy、熊秉真、李焯然、吳根友、鍾彩鈞等人共同發言
首先熊秉真教授憶述「明清研究會」的緣起。該會原先由熊秉真、劉錚雲、梁其姿等學人藉由茶敘與餐會的形式發起,並受到美國漢學家 Susan Mann 等多位學者的鼓勵。
華瑋教授接著說道,在香港類似的國際研討會多以雙語舉行,她的研究生也有舉辦類似的國際型論文發表會,建議中研院明清推動委員會可參考。
Kent Guy 教授說,臺、美擁有同樣的社會基礎、政府與文化,很高興在此地討論明清研究,這是很有意義的。
李焯然教授認為,此次研討會很有意義,學者樂於參加,也帶動了年輕人的參與和研究多元文化的風氣。當跨學科「跨」出去的時候,也許一開始有須磨合之處,但日後會漸漸鎔通。另外,培養年輕後進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中研院實力雄厚,很可惜沒有培養研究生,也許日後可考慮往此方向發展。
吳根友教授表示自己深受中研院明清研究的成果和活力所震撼,目前大陸從事明清思想史的同行不多,需要更多人參與和開發。此次研討會個人已得出許多不同的研究靈感,從熊秉真教授研究器物到思想的變化,觸發他的研究靈感,得知還有許多議題可發揮,比如民間的硯台。大陸沒有明清思想的討論會甚為可惜。
馮爾康教授發言時提到,自己先前在故宮學到許多藝術史的知識,在這裡見識到多元文化研究的知識,讓他體會到學科間交流的必要。本次會議的議題相當具體且微觀,帶給他許多思考。
嚴志雄教授說,此次會議可視為亞洲明清研究國際合作的開端,希望類似的會議未來能在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亞洲的其他地方接續辦下去。此外,由於歐美明清研究的資深前輩學者相繼退休(或行將退休)、世界經濟的重心迅速轉移至亞洲、亞洲明清研究學者已茁壯起來,實力雄厚等等因素,現在正是亞洲明清研究積極發展的契機時刻,應將這種國際學術事業妥善、進一步發展,並期許國際性的明清研究會在亞洲誕生,同時也希望能將一跨地區的學術平台建立起來。
最後,在鍾彩鈞所長的主持下,研討會於傍晚六點圓滿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