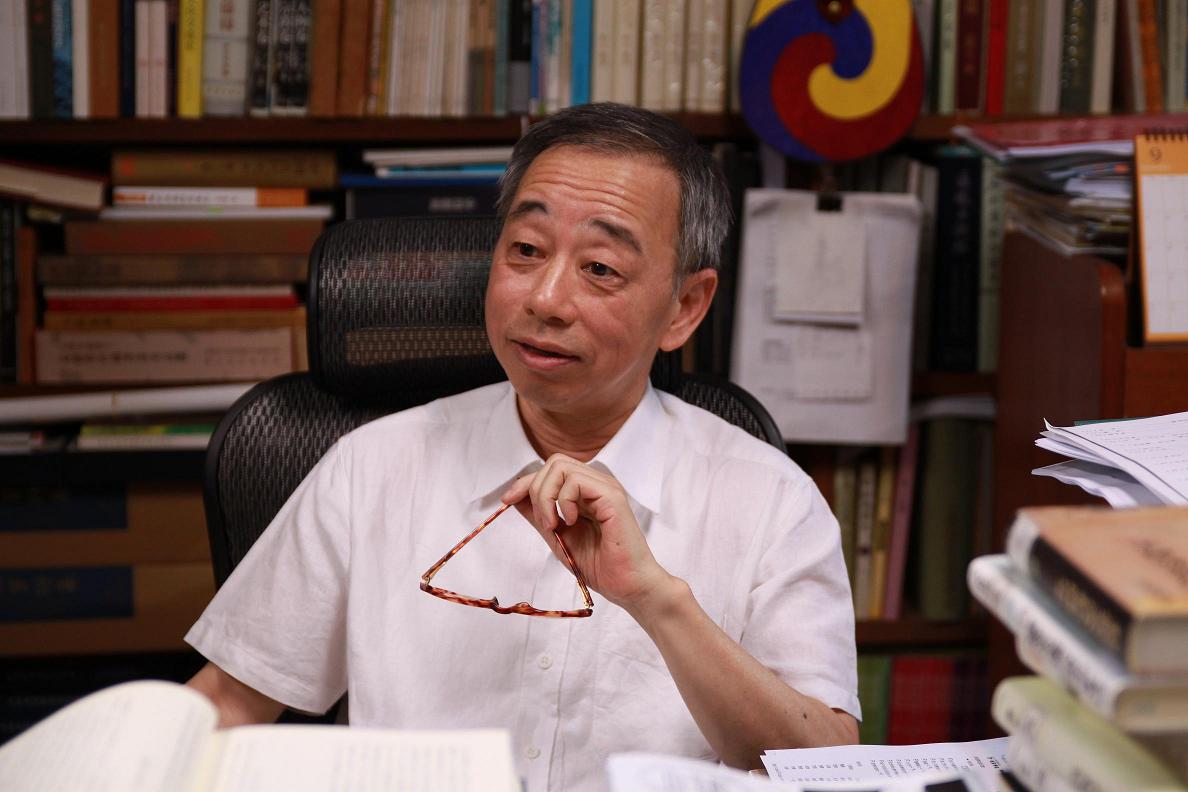專訪石守謙研究員
石守謙教授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倪孟安 採訪整理
英國牛津大學藝術史博士 劉宇珍 協助潤稿
多年來,石教授自文化史的角度,反思中國繪畫史的發展歷程,特別關注畫史上風格轉變的文化脈絡、區域性的畫史發展,及畫史上「雅」、「俗」觀念的互動與區別。其研究成果曾二度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994-96 及 1996-98)。著有專書《風格與世變》(臺北:允晨文化,1996年)與論文多篇,在中國藝術史界享有極高聲譽。近期出版《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繪畫史》(臺北:石頭出版社,2010年),總結近十多年來的研究成果。《明清研究通訊》特於 9 月間拜訪石教授,請他談談新書內容,並分享自己的學思歷程與未來的研究方向。
從「風格」出發,討論世變與畫意
石教授的兩本專著:《風格與世變》(1996)、《從風格到畫意》(2010),均在書名上揭示其以「風格」為討論中心的學術傳承。承襲方聞院士「風格史」的研究範式,他對方院士常提出的「『風格』何以是歷史?」一命題,自有深刻的理解。其對風格史的思考,更深受E. H. Gombrich (1909-2001) 名作 Art and 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London: Phaidon, 1960) 的影響。此書以心理學角度討論風格的形成、延續、與轉變,是風格史理論的經典。書中對風格史的觀點及幾項重要提問,給了他很深的啟發,促使他建立起以風格理論來解釋中國藝術史的研究取徑。究竟什麼是「風格」?石教授解釋,「風格」一詞雖也出現在中國古典文獻,但現在它指涉的概念主要源自西方藝術史,指的是 style,「形式、樣式上的風格」;而「風格史」,即是運用形式分析的方法,分析藝術品的形式、特色,並從中歸納出這些藝術形式自身發展的歷史。風格史家相信,「風格有其依序發展的歷史,而研究者應該去解釋何以有這樣的發展歷程」。然石教授認為,在討論藝術的風格歷史時,仍需探究藝術家創作時的用心,並試圖回歸到藝術家與觀賞者的角度,從他們的理路來瞭解藝術作品。但現今這類研究仍相當缺乏。1996 年出版的《風格與世變》為石教授嘗試「風格」研究的開端,討論「風格」之變與「世變」(指整體社會文化脈絡之變)的關係,探究在不同時代裡,整體文化環境變遷對於藝術「風格」的影響。此一研究取向,試圖從整體文化脈絡來理解藝術史之變的內在動力,實與傳統「風格史」研究認為藝術品的風格發展有其獨立之內在生命,且與外在環境無涉的解釋架構有別。

以圖像學研究聞名於世的學者 Erwin Panofsky (1892-1968) 曾在一名篇中以康德為例,標舉藝術史做為一項人文學科的意義。故事裡,垂垂老矣的康德雖苦於病痛,卻仍掙扎起身,向到訪的醫生致意。緊握著醫師的手,康德欣慰地說:「人文精神並沒有離我而去」。這個故事,帶給石教授極大的震撼,並驅使他往復思索「藝術史做為一項人文學科的意義何在」。他從 Panofsky 的著作中感受到藝術史研究的人文關懷。因藝術史的研究對象,無一不體現著人文主義的精神——在生命萎縮之際、與病魔搏鬥之時、受限於生老病死之自然法則下,仍舊持守不變的信念與價值。
藝術作品的內在意義究竟為何?如何透過視覺或物質形式表達?如何能感動人心?藝術家怎樣設想觀眾的反應?贊助者該如何設定其要求?最後的成品怎樣被人理解?又如何轉化為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進而需要後人以歷史性的角度來理解?這些,都是藝術史這個學科所要探究的根本問題。

台灣的中國藝術史研究
畢業於台大歷史系、台大歷史所中國藝術史組的石教授認為,台灣的中國藝術史研究應自廿世紀中期算起。故宮博物院設院於台北外雙溪並對外開放的那一天,即為一個有系統的中國藝術史研究的關鍵起點。起初,藝術史研究的課程多附屬於藝術創作科系,如師範大學美術系、文化大學美術系等,研究藝術史只是為了配合藝術創作,提供藝術家創作的靈感泉源。直至綜合大學加入藝術史研究的領域,並以較寬廣的人文角度研究藝術的歷史,這樣的情況方才發生重大的轉變,此中尤以台灣大學設立藝術史研究所為轉捩點。
石教授認為其研究取徑和學術研究的發展恰與台灣藝術史學科的發展脈絡相呼應。他以為,藝術院校與綜合大學的藝術史研究是兩個不同的研究取向,此中分別,從各自的出發點與學程設計上便可窺知。藝術科系或藝術院校中的藝術史研究,常傾向以藝術理論和藝術史的研究幫助創作。修習理論課程的目的,是為了讓創作者能有另一層次的表現,故藝術史可說只是創作的附庸,迄今許多藝術院校的課程設計仍未脫離此一基本思維模式。然石教授以為,一個文學家是否要通曉文學史才能寫出一本好的作品,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同樣地,藝術家是否要嫺熟藝術史理論,才能創作出『傑作』,似乎也是個迷思。而綜合大學的藝術史研究則傾向分析藝術品形成的歷程,探討何為藝術、何為藝術品、藝術品何以得以傳世、又何以被視為傑作等問題,進而探究藝術與歷史的關係,以及其與人文價值的關聯,與前者的出發點截然不同。

文人文化與「文人畫」研究
自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藝術史研究亦有其特殊性。傳統的歷史研究傾向以文字、文獻材料為主,視覺性資料多淪為從屬性的「插圖」。事實上,可觸的文物與可見的圖像,都是歷史的一部分,而視覺性的史料數量十分龐大,若能更積極地利用,定能增加我們對歷史的瞭解、補充文獻資料未備之處。史語所成立「文物圖像研究室」之初衷,便是期待史學家能積極利用圖象資料或藝術品從事歷史研究。其研究成果不單能回應藝術史關心的重要議題,亦能幫助我們從不同的視角瞭解歷史文化的種種面貌。故石教授雖與許多前輩歷史學者一樣專注於文人文化的研究,但他更重視圖像等視覺性資料的抉發、詮釋。當從事明代文人文化研究時,首要面對的便是傳統藝術史的基本課題——「是否有所謂的『文人畫』?」一般多主張文人文化的形塑可上溯至北宋,但具體成型在十五世紀以後,主要發生於明代。石教授試著從畫家們的創作思維、畫作的使用方式、觀眾來源與觀眾反應等眾多角度切入,超越風格史的基本關懷,以探究文人畫與明代文人文化的關係。
 以《風格與世變》中的文徵明研究為例,石教授以文徵明代表明代文人文化的巔峰,並將當時的文化氛圍、社會變遷,與文徵明藝術風格之變做一整體觀察,從而突顯「文人畫」與「文人文化」相互形塑的關係、歷程。又如文徵明不屑坊間鍾馗像之庸俗,乃創造出一個新的「鍾馗」圖像,顯示出其有意識地追求並建立特屬「文人」的風格;而此文雅的旨趣、創造,亦隨即為其支持者所仿效。藉由此例,可知文化係由許多具體的、實際的生活層面所組成,故有此「文人鍾馗」像的出現。此外,文徵明為明中葉享譽四方的書家,其書法作品對其時文人文化的形塑影響亦甚大。他書寫大量的立軸,贈送或販售給文化新貴以裝飾彼家中廳堂。因文徵明曾供職北京翰林院,執當時文化界之牛耳,將其書法高懸廳堂,頗有「文徵明是自己座上賓』的意味,整個空間氛圍也因之而一變。此時,文徵明的書法立軸,不僅是裝飾品,更具有特定的文化象徵;而這些新富階級,亦隨之成為文人文化的支持者。
以《風格與世變》中的文徵明研究為例,石教授以文徵明代表明代文人文化的巔峰,並將當時的文化氛圍、社會變遷,與文徵明藝術風格之變做一整體觀察,從而突顯「文人畫」與「文人文化」相互形塑的關係、歷程。又如文徵明不屑坊間鍾馗像之庸俗,乃創造出一個新的「鍾馗」圖像,顯示出其有意識地追求並建立特屬「文人」的風格;而此文雅的旨趣、創造,亦隨即為其支持者所仿效。藉由此例,可知文化係由許多具體的、實際的生活層面所組成,故有此「文人鍾馗」像的出現。此外,文徵明為明中葉享譽四方的書家,其書法作品對其時文人文化的形塑影響亦甚大。他書寫大量的立軸,贈送或販售給文化新貴以裝飾彼家中廳堂。因文徵明曾供職北京翰林院,執當時文化界之牛耳,將其書法高懸廳堂,頗有「文徵明是自己座上賓』的意味,整個空間氛圍也因之而一變。此時,文徵明的書法立軸,不僅是裝飾品,更具有特定的文化象徵;而這些新富階級,亦隨之成為文人文化的支持者。文人文化逐步向外擴展,吸引了許多人的參與,藝術作品則在其間扮演關鍵的角色。石教授表示,透過「畫意」來研究圖像化的藝術品或文物(如分析作品所欲傳達的意涵、探究作品如何與觀眾互動,並衍生仿效的行為等),更能使我們具體地瞭解文化的全貌。

從中國到東亞文化意象的發展願景
早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草創時期,第一任所長傅孟真先生便期許所內學人能發揮「動手動腳找材料」的精神,廣泛使用文物、圖象、藝術史、語言學等材料與研究途徑,以多元角度從事歷史研究,擴展歷史學的維度與內涵。石教授當年自普林斯頓大學學成歸國,進入史語所,即深有感於悠久的學術傳統及多元的研究環境所帶來的刺激與優勢。他在新著中探討有無道教的繪畫風格、道教與繪畫媒介間究竟有無互動等議題,便多獲益於民族所及史語所宗教禮俗研究室等從人類學角度詮釋宗教的途徑。而在跨領域的嘗試中所得到許多反饋,也常讓原本藝術史研究的藍圖更具體地推展與擴大。中研院多元學科的研究環境有利於跨領域、整合型研究團隊的合作。石教授近年執行的「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第十一至十七世紀間中日韓三地的藝文互動」研究計畫,便是一結合文學、藝術史,及歷史研究者的研究團隊,欲藉由文字與圖象的研究,探論東亞的文化意象,並以多元角度重新理解東亞文化史的整體架構。這個跨領域、整合型的研究計畫,試圖反思各別領域對文化意象等相關議題的認識,甚而反思自我研究的認識論、本體論等。其中之一,便是由宏觀的亞洲視角「俯察」自我。若從亞洲的位置看中國,映入眼底的材料,自與從中國看中國的角度大不相同。
 但「亞洲」之概念,源自歐人,本身即為空洞的存在,因此,在討論東亞的文化意象及其形塑前,先要探究「什麼是亞洲?」、「究竟有沒有亞洲的存在?」等問題。然在務實面上,則可先自東亞,即中、日、韓著手。自東亞或亞洲出發,是現今歷史研究的主要途徑之一,目前台灣也有許多研究亞洲或東亞的單位,如清大人文社會中心的「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等,但大抵皆以歷史研究為主,並援用「東亞貿易圈」或「漢字文化圈」等相關概念,這與文化研究領域中的亞洲論述有關。相較之下,「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研究計劃以更具精神層面,比「思想」一概念更具體實在的「文化意象」做為討論焦點,將東亞區域視做一個以文化相繫連的地緣概念,而不單只是物品、資源等物質的流動圈,研究範圍雖較小,但更為具體。目前計劃的發展是將日本、韓國的山水畫材料納入研究範圍,由較廣的「東亞」角度,回應中國、日本、韓國等山水畫史研究中尚待挖掘與回答的疑問。
但「亞洲」之概念,源自歐人,本身即為空洞的存在,因此,在討論東亞的文化意象及其形塑前,先要探究「什麼是亞洲?」、「究竟有沒有亞洲的存在?」等問題。然在務實面上,則可先自東亞,即中、日、韓著手。自東亞或亞洲出發,是現今歷史研究的主要途徑之一,目前台灣也有許多研究亞洲或東亞的單位,如清大人文社會中心的「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等,但大抵皆以歷史研究為主,並援用「東亞貿易圈」或「漢字文化圈」等相關概念,這與文化研究領域中的亞洲論述有關。相較之下,「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研究計劃以更具精神層面,比「思想」一概念更具體實在的「文化意象」做為討論焦點,將東亞區域視做一個以文化相繫連的地緣概念,而不單只是物品、資源等物質的流動圈,研究範圍雖較小,但更為具體。目前計劃的發展是將日本、韓國的山水畫材料納入研究範圍,由較廣的「東亞」角度,回應中國、日本、韓國等山水畫史研究中尚待挖掘與回答的疑問。今年是第一期計畫的最後一年,研究團隊預計以論文集的形式呈現初期的研究成果。未來若能與亞洲或東亞研究等相關諸計劃進行學術溝通,或可進一步帶動台灣對其他東亞區域如韓國、日本的藝術史研究,甚至與台灣既有的中國藝術史研究結合,以中、日、韓的東亞視角進行研究,使中國藝術史呈現更完整的面貌。此雖係遠程目標,但石教授謙稱他願做領頭羊,勉力嘗試,並期許後輩學者繼續努力。

對明清研究的期許
石教授認為,每個學術領域都應有意識地反省、檢討自我定位與價值。台灣一直很害怕自己被世界潮流排斥,更在意自己是否在潮流之中。這是一個值得關心與深思的現象。所有的學術發展都有其世界性,但就學科性質而言則有所差別。相較之下,科學研究的世界性較被突顯,因此科學家很在意潮流。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則有其「在地性」與「特殊性」,很難以單一種學術方法或途徑來處理所有課題,或尋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範式。固然,我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被世界各地的學者關注,不被世界潮流摒棄在外,更不能畫地為牢做其地方型學者。而朝著東亞研究或亞洲研究的方向發展,乃一擴大自我格局的契機,亦不失為一面對「世界性」或「在地性」之兩難的解決途徑。學術組織最重要的是定位問題;立定明確目標,為首要之務。學術組織成員若能有嶄新的目標與共識,共同朝一具體的方向發展,自會有一定成果,也不會與其他組織重複。現今台灣學界的瓶頸在於研討會舉辦頻率太過頻繁,導致學者們疲於奔命,比如與漢學有關的會議一年有 250 場之多,幾乎兩天就一場。學報數量亦不少,但刊物過多反而稀釋了質量,甚而導致學報無法永續經營。過去數十年在國際學術交流方面也花費了許多心力,但成效如何?是否應將動能轉往更值得發展的地方?面對這些問題,石教授認為,如在明清研究一框架內提倡跨領域的整合研究,應當先積極評估學術組織、學報對此領域的效益。他更期許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不只是做為中研院內明清史研究學人的聯誼會,而是更積極地組織、整合各方研究動力,追求更卓越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