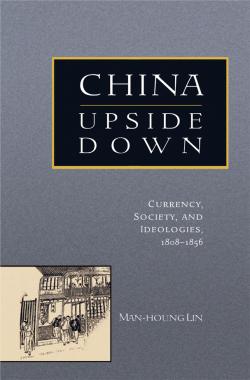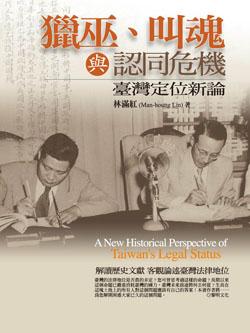|
林滿紅 博士 國史館館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師範大學歷史系所教授
|
|
林滿紅 (Man-houng Lin),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現任國史館館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以及師範大學歷史系所教授。學術領域為台灣史、經濟史、清史以及史學理論。著有專書《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臺灣定位新論》(臺北:黎明文化,2008)、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社, 1997),及其他中英日韓文論文 70 餘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或許是希望我們能更有效的掌握與理解,林滿紅老師細心的在訪談之前,將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中譯書稿寄來,讓我們先行翻閱、研讀,思考提問的方向。初步瀏覽,即感是書牽涉面廣、引用史料繁富,涵蓋總體與個體經濟學、國際貿易、貨幣金融等各方面,又帶入晚清政治情勢甚至經學今古文之爭的討論,統整經濟、貨幣、政治、文化諸面向,以深入探究近代中國歷史變遷的關鍵課題。林老師如何發展出這樣複雜而細緻的研究取徑?撰寫 China Upside Down 一書的歷程與此書回響,她出任國史館館長的抱負,對中研院發展明清研究的建言,以及她未來主要研究計劃,都是我們的訪談重點。
一、研究歷程:立足台灣史,放眼中國史與世界史
林老師就讀碩士班期間,由於受何炳隸教授《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的影響,試圖以計量研究方式,分析清代台灣的士紳與社會流動。林老師先從地方志蒐集資料,再加以統計分析,雖然該報告獲得不錯評價,但總覺如此處理,歷史詮釋的力道尚有不足。於是,便縮小研究範圍,擬以熟悉的霧峰林家為核心探討對象。由於霧峰林家領有台灣的樟腦專賣權,師丈(經濟學家梁啟源教授)便建議老師改以經濟史角度切入。決定題目後,林老師先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找到不全的日文翻譯海關統計,另得劉翠溶教授指點,從近史所微卷找到其他英文海關資料,以此等資料深入爬梳與分析後,林老師發覺:固然,依何炳隸、張仲禮教授之研究,中國社會流動主要倚靠科舉制度,但在台灣,則因買辦與紳商階級之出現,科舉制度之外另出現社會上達的階梯。林老師舉例說,因國際市場的需求,使得台灣山區因樟腦得以出口,經濟價值提高,霧峰林家透過土勇「開山撫番」,林家獲得政治地位,也掌握樟腦產銷的經濟權力。 如此,林老師又意外地回到企圖研究台灣士紳家族的原先構想。透過國際貿易的線索,以經濟學的角度切入,詮釋了台灣士紳家族興起的歷程。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林老師笑道,或許這個研究成果,也可算是進窺台灣史中某一層面的「變」吧?
碩士畢業後,林老師先在淡大歷史系兼課;接著進師大博士班時,林老師又將研究範圍由清代台灣擴充到清代的中國大陸。由於當時李國祁、張朋園教授邀請王業健、侯繼明、劉翠溶等經濟史學者前來授課,所以林老師那段時間的研究成果以經濟史為主。後來林老師遠赴哈佛攻讀博士,初期曾有擇師的兩難,林老師說所幸當時專長社會思想史的 Philip Kuhn 教授主動收她作學生,不然跟著經濟史教授 Dwight Perkins 作研究,可能會加重作計量經濟的部份,而使得自己的學思訓練過度偏向經濟學。在 Philip Kuhn 教授的指導下,林老師感到,「真是熬出歷史的味道來」,遂將原先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納入整個思想文化層面,以是形成日後林老師獨特的研究路數。
二、China Upside Down 的寫作歷程及回響
China Upside Down 是林老師在明清研究領域的一本力作(是書將於江蘇人民出版社中譯出版,譯名《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林老師解釋,書名中的 “Upside Down”(倒置)一詞,本是歐洲史家 Christopher Hill 用以形容 16 世紀宗教改革以降英國社會曾經發生的權威顛置、天翻地覆景況。而林老師認為,19 世紀以前的中國,雖然「多元權威」派(今文經生)的主張不時被提出,但始終無法撼動「絕對君權」派(古文經生)之優勢。而 19 世紀以後,白銀外流,經濟控制權不在君主,而是深受國際市場左右,加上政治經濟紊亂,今古文學派之爭蜂起,真可謂天翻地覆。於是,便有了 China Upside Down 書名的隱喻。
China
Upside Down
先處理清代經濟問題的根源,同時也探討清代政府與知識份子面對「銀貴錢賤」之困境時,所提出的各種對策。就經濟問題而言,該書點出中國白銀外流、世界銀荒與拉丁美洲獨立戰爭
(1820-1830)
間的關連性。林老師表示,當時劉翠溶教授曾提醒道:「在中國白銀外流最劇烈之時 (1830-1856),墨西哥已經獨立,且世界銀產已經開始復甦」。換言之,中國白銀外流危機最深之時,並不是世界銀荒最嚴重的時刻,故需解釋其中原由,否則「白銀外流與世界銀荒相關」的論點將有盲區。因此,林老師透過亞太商貿網絡的研究,在山口大學(前身為山口高等商業學校,主要培養與中國貿易人才)收藏的英國領事報告中找出針對印度用銀的報告。該報告顯示,拉丁美洲銀在獨立運動後,銀產增加有限,仍無法輸出至印度、中國。另老師也從《北華捷報》等資料中發現,上海國外商行的記帳單位從
1856
年開始,才改西班牙銀元為墨西哥銀元。林老師指出,在世界銀產復甦之時,中南美銀產量雖上揚,但仍不足以供應歐美以外的中國需求。而在
1856 年墨西哥「鷹洋」大量輸入中國後,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的現象
才告解決。探知晚清經濟問題的根源後,林老師進一步追問:當時的傳統知識份子,面對「銀貴錢賤」此一經濟問題時,提出的對策與方案為何? 林老師指出,清朝政府規定,一千個銅錢兌換一兩銀子,但市場上往往兩千銅錢才能換一兩銀子。這樣的狀況,連政府、天子都無法控制,「絕對君權」的概念,便受到質疑。所以,就有人提出「有限君權」概念。此即今文經學派有關「銀貴錢賤」對策中所蘊含的概念。林老師認為,從晚清經生因應經濟困境的角度出發,似乎回答了何以今文經學在沈沒一千六百年後又重新興起的原因。 相對地,古文經學派仍主張加強政府控制,並與今文經學派力爭。林老師說,她便是以晚清今古文之爭的視角去研究兩造的交鋒,而這些爭執背後代表的便是自由放任與加強政府控制兩種不同的思想。
林老師又為我們解釋道,乍看之下,十九世紀的中國距離我們很遙遠,但從思想的根源探詢,便可發現,清中葉以降,今古文兩派學者之不同觀點,到二十世紀仍一直有影響力。林老師以最近指導的一篇關於
1960
年代台灣的「費正清賣國集團」的論文為例,發現清末兩派對立的經世思想——絕對君權派與自由放任派,也在該論文的研究對象中看到影子。 在處理今古文兩種思想流派的主張,並描繪各種不同思潮起伏變遷過程時,老師耗費頗多心力與時間爬梳清人文集,彙整脈絡,並將不同的學術觀點類型化,排序成一光譜,而加以討論。只可惜,該書付梓後,似乎並未引起國內外思想史學界的很多回響,迄今書評多偏向經濟層面的探討。 此書出版後,有些國外學人以某些個別經學家之細部思想提出論難。對此,林老師表示:她是將不同的學術觀點類型化,作一光譜陳述,「就如同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般,各黨中份子會有基本教義派,但針對公共議題,也會有比較中立,甚至各式不同的傾向者。故而,分類可能犧牲許多細節,但可突顯特定兩群體的不同特質」,以致不能將這些類型化概念套到所有個別經學家的全部著作上。
此外,有些評者還提及本書索引無法讓讀者「一目了然」。但林老師認為專書索引有不同編法,一種方式是讀者可以透過重要主題詞索引看到本書重要內容,另一種則是任何關鍵詞都按照字母順序表列。是書採用了前者,也就是魏源放在十九世紀學者項下,而不是單獨放在魏源項下,也因為「這本書原有七百多頁,我一直就被要求要縮減篇幅,最後壓縮到四百頁之內;當時雖有助理協助,但光是製作索引即花了我從大清早到深夜的兩個月時間。若我將所有關鍵詞按照字母排序編列,則編排會過於龐大。我採取重要主題詞索引的作法後,卻也造成讀者抱怨搜尋人名等資訊的困難。」 最後,林老師還由此書評論引申出兩項有意思的討論:一是有關「整體觀」的問題。如老師在 China Upside Down 中文版序文中指出:歷史研究可分為有機的整體觀以及機械的整體觀。若研究角度能夠更為有機,則其所能整合的意義便比較大。老師一直希望採用有機的整體觀來研究歷史。用興建公路來做比喻,「有人想蓋平面道路,也有人想蓋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能使車子有機會跑得更快,但卻較難建造、更費工本。」無論如何,史家總是得「依照自己的背景」來抉擇,適情適性,走出自己的路。 二是中日歷史比較的問題。「China Upside Down 還涉及中日關係史。」以中日絲業發展為例,原先是由日本提供中國銀,來交易中國的 know-how,例如絲的製造技術,日本人由此學到經驗。現在的日本絲要比中國的高檔,這其實是有歷史原因的。老師繼續解釋:「在 1850 到 1880 年間,白銀回流,景氣好,很多中國人覺得技術不用進步也能過得很好。也因為當時中國仍掌握絲的國際市場。相較之下,日本要擠進市場,就非得拼命提昇技術不可。於是,一靜一動,兩國的技術差異就逐漸明顯了。」
三、經世致用的自我期許與就任國史館館長
林老師一直都認為,知識份子應該關心時政,將知識貢獻社會。在接任國史館館長後,對國史館的定位與發展有新的見解。她認為國史館在傳統史料編纂外,更應發展其經世致用的淑世功能,一如 China Upside Down 中今文經學者希望透過歷史解釋傳達思想。
關於台灣島移轉中國事,英國政府以為仍應按照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之開魯宣言。同盟國該項宣言之意,不能自身將台灣主權由日本轉移中國,應候與日本訂立和平條約,或其他之正式外交手續而後可。因此,台灣雖已為中國政府統治,英國政府歉難同意台灣人民業已恢復中國國籍。
這裡的中國政府當然是中華民國,但從當時英國政府「歉難同意」云云來看,日本戰敗歸還台澎給中華民國,就國際法來說,仍需透過正式條約合法移轉。所以,台灣在法理上真正的回到中華民國統治,要俟 1952 年中日和約才算確定。林老師表示,她的論點在國內造成許多責難,但批評者未曾細讀她的研究而進行理性的討論,多為情緒性謾罵,殊屬可惜。關於台灣地位,儘管國內爭論不休,但中日和約的照片顯示日皇業已付印,即便當年的日本國會對此多有爭論,仍舊無法掩蓋和約為一合法文件之事實。 中日和約的第十條說:
就本約而言,中華民國國民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而具有中國國籍之一切台灣及澎湖居民及前屬台灣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後裔;中華民國法人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所登記之一切法人。
這裡的法律文字雖然拗口,但基本上說的包括老台灣人與新台灣人兩種自然人以及單位法人。由於當時是在移轉領土,領土不只是土地,也包括土地上面的人與物。根據這條法律,臺澎地區的人都可以依照中華民國法律成為中華民國人,這也包括越南新娘等等。這情況一如美國國土上的人都可以依照美國法律成為美國人。就此,林老師進一步申論,現在的族群問題,可說都是由人們心理所構建出來的危機。若能由中日和約切入,族群的身份問題不啻可獲解決?
此外,為了讓國史館具備更積極的學術作用,林老師上任之後,便創辦了國史館學術獎助 (http://www.drnh.gov.tw/www/page/F/990125/poster.htm),鼓勵各方年輕學者透過參賽,貢獻、累積更多的研究心得。老師指出,「國史館每年用一百三十萬來獎助這些關於中華民國史的、台灣史的基礎研究。入選的專 書獎助金為十萬,論文則為三萬,質佳者可優先出版。去年有卅二本參賽,今年也有卅二本參賽。這樣的活動會一直辦下去。這樣累積下去,國史館就不只是出版資料彙編,也會有研究成果。」老師說「透過研究才能瞭解這個時代。而且,在審查作品的過程中,台灣學界也可以與國際學者、資深學者交流。」談到這裡,林老師也建議能成立明清研究獎助,獎勵學術研究成果出版,也獎助年輕學人到國際會議上宣讀研究成果,這對提昇台灣明清研究將會很有助益。
四、對於中研院明清研究的建議
林老師也強調中研院培養後進學生的重要性。她在研究院時經常建言要鼓勵研究生作「歷史的基礎研究」,因為藉由學生來進行基礎性質的研究,便能有效地累積學術研究的厚度,並讓具有豐富研究經驗的學者、研究員能進行宏觀、整體視野的整合型研究。林老師就自己的經驗指出:「在研究中,總是會有很多分枝出去的子題。既然有這麼多的明清學者在中研院,他們思考、研究所觸及的子題,就可以交與年輕學者(或研究生)去做,這樣他們的研究也才能撐得大。」就此,林老師以自己指導的論文為例,如鄭永昌的碩論即專注在處理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議題,可與 China Upside Down 一書中所討論道光年間的「銀貴錢賤」對話、呼應。爾後,鄭的博士論文進一步研究了乾隆年間的銅錢制度,從中看出當時鼓勵私鑄銅錢的現象,這也支持了林老師的研究。此外,另一位學生林志偉作乾隆年間的馬政研究,研究成果也被 China Upside Down 所引用。老師說道:「大清王朝原來是草原民族,對馬是很有概念的。相較於明王朝,清朝在馬政上很有進展;明朝本身沒馬,要用還得跟北邊常給自己帶來威脅的蒙古民族去買。清王朝一開始就與蒙古聯姻,旋即有馬可用。乾隆打下新疆後,又有哈薩克馬可用。馬是清代整合帝國很重要的基礎,一如銀子一樣。…… 1661 年起 清朝規定大宗交易必須透過銀子,可是在《皇朝經世文編》所收十八世紀的貨幣討論,都是在討論銅錢,銀的相關討論幾乎是不存在的,這讓銀最後成為清朝的阿基力腳後跟 (Achilles’ heel)。我的研究,由馬政研究來對照,可以更為立體。」上述例子都有力的說明了,學者帶領研究生作研究,成果不止於教學相長,更能達到林老師所謂「撐起整個領域的基本間架」的境界。
林老師補述道,自己指導過的近四十個學生,主要還是因個人興趣、背景而協助學生進行研究,並不盡然都要求以經濟史角度切入,也有從法律、社會、政治等面向切入研究的。如林老師的學生陳燕如,研究基隆中元普渡,發現因為日治時代的基隆,較諸台灣其他城市,日人比例最多。基隆在地方望族的領導下,透過中元普渡來加強自我的凝聚力,而日本人也透過這些地方士望族溝通協調,推行命令。因此,中元普渡在基隆地方,有其獨特而深刻的意義。林老師認為,這樣的研究,既涉及經濟,也關乎文化層面的探討,「這些都是我的路數」。老師笑著解釋,「沒有說非要修經濟學才能進行研究這回事」。 有關培養後進學生的問題。林老師也特別指出:研究院本來就可以招收研究生。在 1928 年創院之後,中研院即曾收錄研究生。而遷台之後,中研院招生的相關辦法也並未更動過。在 1995 到 1998 年之間,林老師參與了院內修法工作,但當時即發現立法院討論《大學法》時,研究院竟然沒有參與!林老師向院長報告本院其實本有法源可以招收學生授予學位,可惜只有大學可以招收學生的《大學法》已然通過。不過,話說回來,林老師認為中研院收研究生也並非有利無弊,「因為中研院沒有大學部,無法孕育出較完整的校園文化」,研究生部有配套的大學部教育,才會有比較健全的發展。在此現狀下,林老師鼓勵院內應多與大學合作。
五、研究苦樂與未來方向
問到近來的研究方向與規劃時,林老師說她正計劃出版「土產鴉片與晚清中國」(Native Opium and Late Qing China) 與「台商的亞太經貿網絡 1860-1960」(Pacific Bound: Taiwanese Merchants’ Overseas Network, 1860-1960)。關於這項研究主要談論香港、台灣與太平洋間的商業網絡。老師解釋道:「香港,是大英帝國在亞洲的中轉站,而日本帝國如何把台灣建立成在大東亞的中轉站,與香港競爭,是這個研究的重要課題。……研究中可以觀察出,在日本帝國一連串行動背後,是一個崛起中的太平洋。我主要是以這樣的海洋角度將台灣研究與世界史串連起來。」
最後,老師也分享了她最近因應邀稿而寫的一些小文章的心得。「我剛剛完成一篇文章,是岩波書店邀約寫的,他們要我寫一篇關於『1930
年代台灣在亞洲內部的人流與物流』的文章。……我用了總督府檔案,因為邀稿中特別要求我在文中觸及日治時期台灣與朝鮮的貿易,原來我的研究沒有包括這一塊,於是我便補上。從中發現一件饒富趣
尾聲
最後,感謝林老師在授課、研究與館務的百忙之中,接受我們訪問。這次訪談中,我們除了更理解林老師紮實認真的學術內涵,同時也感受到老師以史學家自許的經世熱忱。
__________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倪孟安 黃咨玄 劉威志 整理報導
|
 碩士期間的研究成果,先由台銀以《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碩士期間的研究成果,先由台銀以《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