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麗月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任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東京大學文學部外國人研究員,現任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研究專長為明代史、明清社會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明代的國子監生》、《明末東林運動新探》、《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除此之外,並有〈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基層社會〉、〈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孝道與婦道:明代孝婦的文化史考察〉、〈科場競爭與天下之「公」:明代科舉區域配額問題的一些考察〉、〈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等數十篇論文發表。
師大求學經驗與學術啟蒙
「我在學術領域開竅、學習,是從研究所才開始的。」林教授謙虛的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於民國五十九年創立,林教授於民國六十一年入學,是第三屆的學生。當時,林教授的指導教授李國祁擔任第二任所長。李教授在創所階段,聘請了很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輩老師到師大任教,讓林教授覺得念研究所的天空和大學很不一樣。
回憶起當年還是碩士生的上課情景,林教授笑著說:「那時候我們一屆才五、六個人,各自選課的結果下來,一班可能就只有一兩個同學,如果上課講不出話來,就真的只能和老師大眼瞪小眼了。」在碩士就學階段,林教授對李國祁、張朋園、王爾敏、毛漢光等幾位老師的教導印象特別深刻,說到他們對學生的要求非常嚴格,也相當重視上課的討論。這種學習經驗和大學時期被動的聽講大異其趣,林教授認為正是這些老師靈活的「研討班」(seminar) 教學,培養了她主動想問題、問問題的習慣,對她往後的研究之路有莫大的助益。
同時,林教授也深信這些師長們,尤其是來自近史所的幾位老師,影響了師大歷史所的學風。「當時,是史料學派興盛的時代。」林教授遙想當年,認為這些老師嚴謹的治學方法與對史料所下的功夫,無形中潛移默化了師大歷史所的學風。這個影響至今無人可以否認,也讓林教授感念不已。
碩士班畢業以後,因當時出國風氣盛行,林教授也曾興起出國攻讀博士的念頭。但因為顧慮到父母的負擔,師大又剛好設立了博士班,最後還是留在師大繼續深造。民國六十六年進博士班的林教授,同時在師大歷史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工作內容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助教一職。林教授回憶起當時擔任所長的李國祁老師,總是嚴格要求助理研究員必須利用公餘時間多看書寫作,一刻也不得鬆懈。而這些往事林教授現在想來,卻覺得一邊工作一邊念書,真是莫大的幸運。
林教授就讀博士班期間,適逢師大歷史所延聘多位海外學者擔任客座教授。林教授前後修習聆聽過幾位著名的經濟史學者,如侯繼明、王業鍵、劉翠溶的課程;在思想史方面則有汪榮祖教授的課程。這些老師對林教授的學思歷程有很大的啟發。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老師的課程,引領她接觸到當時美國比較新的研究趨勢。西方學者的研究,相對來說比較重視理論架構,怎樣從自己看的史料裡建立一套解釋,對於本來比較不擅於思辨的學生而言是相對困難的,而這些老師的引導就顯得格外重要。另一方面,林教授也指出這段修習經濟史、思想史課程的經驗,讓她更加體認到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政治史其實都互有關涉、不可分割。回首碩士班的這段受教過程,林教授說:「因為歷史是整體的,所以我的求學經驗可以有這些不同領域的專家給我如此嚴謹的訓練和啟發,我覺得很幸運,對我自己的獨立研究很有幫助。」接著,林教授也與我們分享了年鑒學派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曾說過的一句話:「社會史和經濟史都不存在,只有歷史是存在的。」提醒我們,「整體史」的概念,雖然現在看來是尋常道理,但在研究實踐時卻是不容易達成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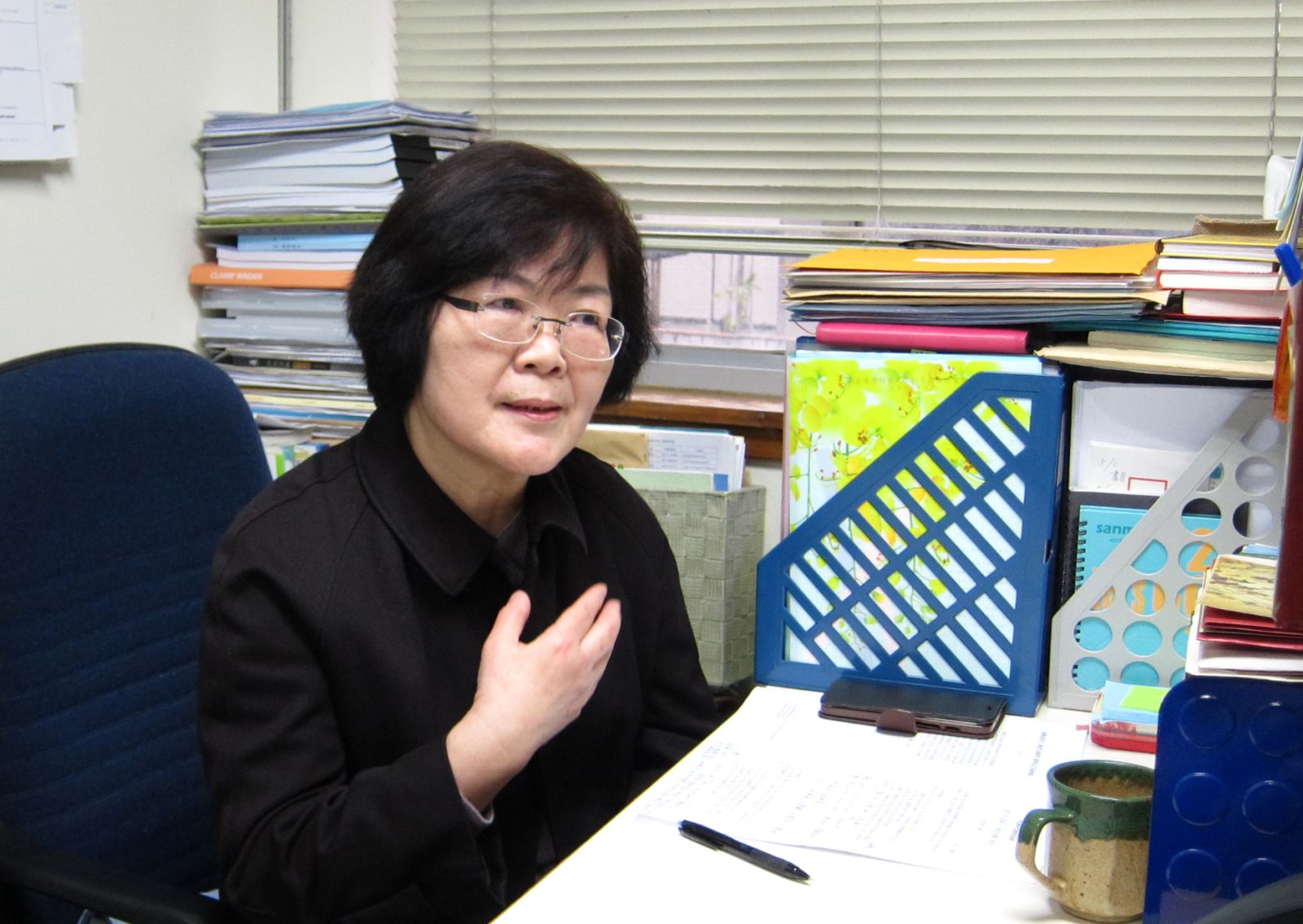
走進大明天地
林教授表示,自己投身明史研究,原是很偶然的機緣。當時她的多數同學都做近現代史、特別是晚清史方面的研究,而她自己在碩士班階段也修習了很多近代史的課。但一方面因為自己始終好奇中國在十九世紀面臨思想、社會、政治、經濟變遷之前,到底是什麼情況;另方面,也總是堅信著,長遠的時間之流不會讓這段歷史忽然冒出這些變化來。再者,也想著總該有人做前近代的課題。所以,當時的林教授一直對十七、十八世紀之前的中國社會面貌感到興趣。
猶記得是碩一的暑假,林教授在閱讀史料之際,發現明代的國學(太學)是個很有趣的題目。他注意到明初國子監生的政治出路寬廣,和晚明、清代國子監生的處境判若雲泥。她將這個觀察告訴李國祁老師。李老師一聽,大表贊許,並且慷慨應允指導。
於是,林教授以「明代的國子監生」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1] 而她對這一課題的想法,更是和李國祁老師的期許不謀而合,亦即將「明代的國子監生」當作社會史來進行研究。林教授表示:「當時美國流行的社會史深深影響了我們這一代,尤其是社會流動議題和量化方法。我們幾乎每個人都花了很多時間看何炳棣、張仲禮的研究。」雖然明初國子監生的問題,必須先從制度層面入手,但林教授很篤定的說:「我當時就想,我要做的是『這群人』,看他們在明代的社會、政治角色,勾勒他們的地位升降變化。」
到了博士論文階段,林教授回憶當時老師們多鼓勵研究生做大題目,她對思想史方面較有興趣,因此選擇「明末的東林」作為博士論文。[2]「東林好像是大家很熟悉的主題,但實際上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大題目,不僅牽涉到很多士人,綿延的時間又很長。我當時是受到賀凱 (Chares O. Hucker) 那篇明末東林運動論文的啟發,基本上,我的思路是將這群人在萬曆至天啟期間的思想與行動,有如賀凱所說的當作運動 (movement) 來看待。」[3]
林教授博士論文《明末東林運動新探》的論述重點分為兩部分:其一是從制度層面看東林運動興起的背景,以及東林運動實際上在晚明政治中引起的問題。林教授強調:「看起來我好像是在做黨爭史,但其實我比較注重的是制度上的原因和制度中的人。」其二則是著重在思想層面的探討,主要是考察東林人士怎麼樣看他們身處的時代問題,包括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野時的言論。
林教授提到當時學界與東林黨有關的研究,多為中文系的教授聚焦於東林黨人的思想,比較偏重哲學思想的分析;另外還有一些中國大陸的學者留意東林,但著重於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市民運動」或「啟蒙思潮」的詮釋。林教授的研究則是從廣義的思想史切入,探究這些士大夫如何看待內閣與六部的制度摩擦問題,他們和君主、宦官的權責關係,以及他們在當時的制度中如何實踐他們的理想。林教授不贊成研究者為歷史人物(特別是一群人)貼上階級屬性的標籤,她認為研究人數眾多、群體邊界模糊的東林人物,最重要的還是進到晚明政經社會變遷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透過他們的議論與思想,來觀察他們所處的社會,這些被指為「東林黨人」的士人,識見立場未必一致,卻恰好給我們研究者更生動的圖像。
「讀書人的思想就像一扇窗,讓我們看到那個時代動態的歷史樣貌。」繼博士論文之後,林教授所發表的福建食米不足問題、明清之際商業思想、東林運動與晚明經濟等論文,都反映了如此的研究關懷。她認為,很多問題的各個面向都是相互繫聯的。也就是說,思想史的研究不應該與政治、經濟面向的探討切割得如此涇渭分明。林教授謙稱這樣的心得,來自於她一個最原始的初衷——「我只是基於對知識分子心靈世界的強烈好奇,希望透過耙梳他們所留下的文字資料,能更貼近他們的時代與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社會與思想的交光互影
林教授過去的研究包含了選舉制度、社會流動、經濟思想、性別文化、遺民認同等課題,她曾在他的新書自序中談及她的研究關懷,主要在於「社會與思想的交光互影」。[4] 藉著這次訪談,她也和我們分享了她在研究之路上的所見所思。
「我的老師們都曾做過紮實的制度史研究。」這是林教授在早期的作品中,專注於制度變動、制度與社會關係的原因之一。林教授認為,制度不是死的,而是人為了統治管理而要求人群遵守的規則,也正因為制度是因治理需要而建立的,所以也會隨政治社會等方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林教授提醒我們:「在研究的過程裡,每個人都不該輕忽對重要制度的了解,因為制度的變化,實則反映了一個社會的變化。」從林教授對明代國子監生、察舉制度、科舉區域配額等研究即可看到,制度變化是觀察明代社會動向的絕佳窗口。她以科舉制度為例說到:「科舉,它絕不是一個只有框框條條的制度,它牽動了宋代以來,尤其明清士人的政治出路、社會流動、學術思想、價值觀念,甚至日常生活。這麼重要的制度,我們透過當時人對科舉改革的關注和論爭,如鄉試的解額、冒籍問題的討論,可以解答過去研究沒有注意的角落,反映活生生的社會百態。」
1980 年代以來,林教授發表了許多思想史的論文,其中包含了經濟思想、社會風尚、遺民認同等問題。林教授歸結她之所以發展如此「駁雜」的研究主題,原因在於她對知識分子保持高度好奇,因此不斷追索士大夫的足跡來做研究。她指出,十六世紀以後的明代出版業格外興盛,文人文集除了各種坊刻本,還有很多家刻本流傳,研究者需透過這些材料,才能窺探明代士人眼中的世界。林教授以她一系列討論明代社會風尚的作品為例,說明明末士人批評奢侈,但事實上奢侈是有原因的。她研究的「崇奢論」,也許不能用「崇尚奢侈」、「反對節儉」來理解,卻是若干士人對禁奢令極具反省意義的觀察。像陸楫 (1515-1552),就是去理解奢侈的原因,進而希望執政者能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士人。[5] 又如,林教授注意到明中葉以後頻繁出現的「服妖論」,由此探析晚明的服飾風尚,及「服妖論」的思想文化意涵。[6] 她強調,明末士人批評奢侈和「服妖」的聲音很多,但研究者不能忽略這些批評本身就是一種當代的「社會觀察」:「士人面對他們所看到的世界,有的發抒感慨,有的嚴詞批評。這些感慨或批評,用傳統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往往被認為是保守的、充滿儒家教化思想的『道德說教』,但這些記載其實映照出社會的實際情況,有非常豐富的社會史價值。」林教授的一席話提醒我們,士人對「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感嘆,無疑是活生生的社會史素材,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史與社會史的意義。
林教授在某些論題的拓展上,還來自於一段教學相長的佳話。「衣若蘭教授是我第一個指導的學生,她對性別史有著高度的興趣。在指導她論文的期間,我透過與她頻繁的討論,無形中開展了對明代婦女史論題的關注。」林教授回憶當年指導衣若蘭教授完成碩士論文《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彼此教學相長的愉快過程,也談到自己的婦女史研究心得。林教授認為,不論是「婦女」或者是「性別」,都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對她而言,注意「性別」讓她有如多了一隻眼,幫助她觀察到社會中更多元的層面。「很多研究受到專門化、分科化的影響而做了不必要的區分,事實上,這些課題往往聲息相通,不應該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不論是《杜騙新書》還是『孝道與婦道』,[7] 我其實都把它們當作社會史在研究。」林教授再次謙稱,她不是婦女史專家:「我只是透過婦女或者性別的角度,將我對這個社會不清楚的部分填滿,希望藉此達成深入考察明代社會的目標而已。」
最後,林教授為自己的研究關懷作了一個小結。林教授希望能透過自己一篇又一篇的研究,如拼圖一般,呈現出明代的社會圖像。她強調,明代和近代史很不一樣,明代過去被視為傳統社會或帝制中國的晚期,與清代以至近代中國有連續,也有斷裂。從柯睿格 (E. A. Kracke) 提出的「內變」(change within tradition) 來看,不論是把明代界定為「近代早期」或「帝制晚期」,明代這個「傳統」,今天看來仍然深具意義:「如果我們對傳統都不能有些理解,就要談傳統與現代有什麼不同,我認為那就真的有點『奢侈』了。」

未來的研究方向
不斷開展新的研究領域,對於寫作樂此不疲的她,也和我們分享了最近正在研究的課題。林教授這幾年忙著撰寫明代地方廟學的專書,其內容主要是透過地方儒學來看地方認同,聚焦於學宮禮制、地方祀典與基層士人的關係,以構建一個以廟學為中心的社會文化史。林教授注意到明代鄉賢祠與名宦祠在廟學系統中的制度化,特別是明代開始限定本籍人士才能入祀的鄉賢祠。林教授在「俎豆宮牆」一文中強調,明代地方廟學中祭祀「不待遠訪」、「至親且切」的鄉里人物,其豐富的在地性與親近性,在匯聚地方情感與文化認同上的作用為中央祀典所不及。但明代中期以後,鄉賢推選不當、賄求冒濫之弊層出不窮,以致士大夫反以入祠為辱。鄉賢冒濫問題的背後,存在著基層士民與地方官紳的微妙互動關係,其間的角力、衝突與妥協,正是地方廟學與明清社會生活緊密相繫的寫照。[8] 此外,林教授以廟學為中心,搜羅修纂方志的地方士人資料,藉此試圖重建修纂方志工作背後的權力運作過程。她認為,透過各個地域基層士人參與地方志的修撰,可以看到他們如何看待地方史,用什麼方法書寫鄉里故事;其中當然也牽涉到文化權力的問題,什麼被收錄,什麼卻被刪除了。這些都是林教授撰寫中的新書關注的重點。
延續關於基層士人的話題,林教授用似乎帶有一種使命感的語氣說到:「我覺得過去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學術思想史,往往聚焦於非常有名的大學者,例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大儒,或王陽明等有學派的理學家。如果我們同意思想史需要更進一步的擴展與深化,我認為有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小儒』的研究。」
林教授所指的「小儒」,不是黃宗羲〈原君〉中批評「小儒規規焉」的見識淺狹的士人,而是相對於「大儒」的比較不知名的讀書人。對林教授而言,這些讀書人其實也是受過基本儒家養成教育的「學者」。「小儒」和前述的大儒一樣,有他們心中的理想世界,而要重建他們的歷史,就必須從地方社會去找。
林教授指出,地域社會一直是明清社會文化史很重要的課題。明代中期以後,科舉競爭日趨激烈,壓縮了很多人往上考取功名的空間。「年輕時,我在何炳棣的研究中,看到一頁又一頁因科舉造成社會流動的統計數字。現在我要追問的是,那些科舉挫敗的個案,那些在研究中被化為數字的人物,他們後來到哪裡去了呢?我想為這些小儒勾勒他們的生命史。」林教授充滿溫情的訴說這段研究的心路歷程:「在晚明,有很多士人待在家鄉。他們可能做過很短期的寒傖小官,如教諭、訓導,做了幾年以後,回家鄉度過漫長的餘生。」林教授具體舉出最近正在考察的吳江人莫旦為例,描述莫旦正是具有這樣特色的士人。莫旦為成化元年 (1465) 舉人,一生主要的任官履歷是浙江新昌訓導和南京國子監學正。活了八十幾歲的他,編了很多方志。話鋒至此,林教授略帶欣喜的說:「莫旦就是我說的『小儒』。我很好奇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麼,心目中的地方秩序是什麼。我希望透過他的著作,可以開啟地方社會史甚或知識史的另一扇窗。」
林教授堅信,關於這類「小儒」的研究如果累積得夠多,應該能提供思想史研究,或是明初到晚期,甚至明清之際的歷史變遷過程一些養分。她語重心長的表示:「現在的我,已不再像當年那樣想做所謂『大題目』了。因為從大處著眼,不免會忽略大社會的個人。個人的生命經驗、不同地域對這些士人的影響,是我接下來最關心的議題。我認為從個別的人物切入,慢慢累積小儒的研究,能夠使我想探究的時代特色與地方社會面貌慢慢顯現出來,可以讓人群與明清社會的關係更趨立體的呈現。」
給研究生的建議
長期在大學任教,有著豐富教學經驗的林教授,在訪談的最後,也給了現在研究生三點由衷的建議。首先,林教授提醒研究生,治學的根本最重要的還是史料;建議研究生要在史料上下功夫,多讀古籍文獻,不僅要多讀,還要精讀細讀。她特別提醒有志於明史的研究生:「治明史,除了努力尋找新資料外,更重要的是,要在看起來極為普通的舊材料上,逐字逐句反覆的閱讀,唯有這樣,才能在看似尋常的一般性材料中發現新的問題。」她感嘆:「明人文集就不是什麼新史料,但還有多少文集我們還沒有好好讀過啊!」由此提醒研究生要「耐煩」,要持續的在文本上下苦功。
其次,在事事 e 化的今日,林教授建議研究生有機會還是要去圖書館看書,在書架前尋訪一本一本的實體書,「透過這樣的瀏覽,你可以看到它的『隔壁』是什麼書,或許就有機會找到一份相關的文獻,甚或發掘一部學界從未注意的史料。」林教授表示,這絕對是只靠關鍵字查詢線上資料庫達不到的效果。
「不要跟風追新」,是林教授最後一點的忠告。這幾年她觀察到,不少研究生會以哪個領域現在比較熱門為基準來選定論文題目。林教授表示,研究生選題優先考量的應是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唯有找到與自己才性契合的議題,才能在學術研究的路上走得長久。從一個國家史學發展的特色來看,林教授更認為研究「趕時髦」絕對不是一個好現象。腳踏實地、甘於寂寞,才是史學志業最核心的本質。

[1] 林麗月,《明代的國子監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出版,1978。
[2] 林麗月,《明末東林運動新探》,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
[3] Charles O. Hucker, “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132-162.
[4] 林麗月,《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臺北:新文豐,2014.10),頁ⅱ。
[5] 參見林麗月,〈陸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年明清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新史學》,5 卷 1 期(臺北,1994.03),頁 131-153。
[6] 參見林麗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新史學》,10 卷 3 期 (1999.09),頁 111 - 157。
[7] 參見林麗月,〈從《杜騙新書》看晚明婦女生活的側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 期 (1995),頁 3-20;林麗月,〈孝道與婦道:明代孝婦的文化史考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6 期 (1998),頁 1-29。
[8] 參見林麗月,〈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的基層社會〉,收於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327-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