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廉明教授演講「北京天主堂:1600-1800 年間的宗教及跨文化空間」紀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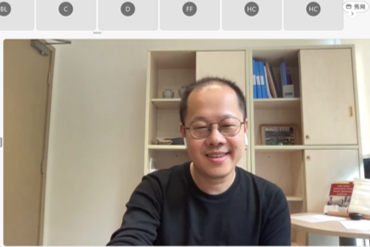
|
本場演講為中央研究院「西學與中國」研究群「星期一讀書日」新書演講系列的其中一講。王廉明教授畢業於德國海德堡大學,目前任教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本次演講以王教授的新書 Jesuitenerbe in Peking: Sakralbauten und transkulturelle Räume, 1600–1800 [Jesuit Legacy in Beijing: Sacred Buildings and Transcultural Spaces, 1600–1800]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2020) 為中心進行。
演講伊始,王教授首先對北京天主堂的研究進行回顧,指出對天主堂的專門研究從 1930 年代就已出現,不過在後來一段時間處於沉寂狀態,最近又有幾本研究著作相繼出版,顯示學界對此日益高漲的興趣。
接著,王教授從傳教士的書信著手,考察北京三個天主堂的建堂史。在南堂的案例中,其土地並非整齊劃一的一整塊,而是由來源各有不同的幾塊地合在一起,其中既有利瑪竇早在明代時就已經購入、作為教會的私產地,也有臨近一塊原先作為首善書院(即東林書院北京分院)用地,後被湯若望等人在編撰《崇禎曆書》占用的部分。入清後,為補償清軍入城時燒殺搶掠所造成的損失,清廷將這兩塊地中間的隙地和後面的地都撥給教會使用,日後這兩塊地就變成天主堂和後花園。由此可見,南堂的土地所有權處於相當混雜的狀態。在東堂的案例中,東堂宣稱自己是由皇帝所勅建,腳下的地皮是朝廷的賞賜,還立了一塊「勅建」的碑,但其實對於清宮而言,這塊原屬於禮部的地之所以撥給教會,是基於對西人遠道而來的一種優待,是公共財而非教產,耶穌會與清廷兩者之間屬於各說各話的狀態。至於北堂,其土地是法國傳教士從朝廷手上得到的一處大臣廢棄宅邸,而後教會又得到旁邊一塊更大的地。這塊地原是康熙皇帝撥給法國傳教士,用以建設植物園,但教會挪用了其中一片來建天主堂,並宣稱是「勅建」,即以建科學園之名,行傳教之實。總結而言,南堂、東堂、北堂的土地,其實只有南堂一小片明代購置的土地是教會私產,其餘也多不是教會所宣稱的「勅建」。
既然土地產權的問題如此多,那教會何以敢於天子腳下宣稱自己的所有權?王教授認為,耶穌會充分利用了皇帝的權威,他們在天主堂前建立碑亭,碑文內容雖與皇帝有關,但卻是出於一種刻意的曲解而刻於碑上:一塊碑上刻的順治帝答覆天主教文,然而該文並非是認可天主教,而僅是一個泛泛的答覆;另一塊碑上刻的「容教令」其實也不是允許宣教,而是皇帝的備忘錄 (memorandum),並非政令 (edict),皆不具備正式的法律效力。這些碑存在的意義其實是皇帝聲音的展現,耶穌會士將其視為一份皇家大禮,上石立碑並放置在教堂空間中,體現出一種紀念碑性 (monumentality),並為所謂的「勅建」提供合法性背書,至於具體的文本內容,其實並不重要。類似的做法還展現在其他與建築相關的藝術形式中,譬如對聯和牌樓,它們都以其在中國脈絡中具有的紀念碑性,而為存放這些紀念物的教會空間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傳教士對文本的曲解不僅是對中國受眾,對西方受眾也做了類似的操作,傳教士將新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意涵進行了極大的曲解,並挪為己用。耶穌會傳教士對紀念碑性進行操作的另一個重要維度是時間,日食鐘、沙漏鐘這些報時系統在耶穌會自己的體系中本就擁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國的帝制中皇家對世間萬物進行控制的重要一環,屬於合法性的一部分。耶穌會在北京的教堂使用了大量的鐘,在城市空間中與朝廷的傳統鐘鼓樓報時系統進行競爭。
再者,王教授將研究目光轉向建築。一般來說,耶穌會會對其興修的建築進行審核,因此耶穌會經常被認為對建築保有很高的控制權。但是北京南堂其實並沒有一般教堂的穹頂,它的內部空間也沒有西方教堂那麼深,這些改動是葡萄牙教團的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 所作,目的是為了在頂上繪製幻景畫,以此與法國教團競爭;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也是出於在南堂天頂繪製幻景畫的任務而來華,其繪製的幻景畫成為日後清宮幻景畫的起源。徐日昇在建築空間上的改動是有意識的,這樣能夠讓觀者甫一進入教堂就能處於天頂幻景畫的最佳觀看位置。至於建築外觀,南堂和東堂都屬於葡萄牙傳教團,外立面是一種網狀的分隔方式 (cluster)。這種做法不是耶穌會通常採用的方式,而是文藝復興晚期矯飾主義常用的做法,日後由於書籍的傳播而在葡萄牙語國家較為流行。這些葡萄牙式的裝飾風格在印度果阿 (Goa) 地區出現新的發展,他們做出一種環環相扣的格子狀外立面,如今澳門尚可見。南堂和東堂在建築樣式上與北堂的差異,顯示出在全球語境下,耶穌會建築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分散的集合體,其中有葡萄牙式、法式,甚至還有義大利的建築樣式,耶穌會對各個國家教團的約束力並沒有想像中來得大。
談及耶穌會諸多藝術與技術進入清宮的管道,舉例而言,十七世紀前期,基督教在圖像學意義上為數不多的幾種主要圖像,其實都是從澳門出發,沿途經過肇慶、韶州、南昌、南京、濟寧等地,最後抵達北京。各種幻景畫也是先在教堂空間進行試驗,而後再通過像年希堯 (1671-1738) 和郎世寧這樣的人物進入清宮。在清宮的部分,王教授著重探討了圓明園中的湖東線法,過去的學術研究認為,湖東線法是通過畫片排列,在特定的視點中看到歐洲城市景觀,但王教授認為「湖東線法」之所以會有「湖東」之名,是因為線法山和「湖東線法」之間的湖是被作為中國傳說中的「東海」來理解的。因此,這些線法其實是要表現不真實存在的海市蜃樓,而線法山上建築的造型,以及清宮工藝品上的類似圖樣,也會讓人聯想到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仙閣。至於線法山旁的遠瀛觀,是整個西洋樓建築群中最後興修的建築,它並不僅僅是用來存放西洋奇珍,還作為西洋樓建築群中的觀望臺使用,左看海晏堂,右看線法山。遠瀛觀的「瀛」也與中國傳說中的仙島瀛洲有關聯(圓明園福海中也有名為瀛洲的小島),瀛洲在傳說中就是充滿珍寶的地方,可以與遠瀛觀的功能相扣合。因此,西洋樓景區其實是以中國古代傳說為概念框架,來再現「西洋」的概念。
此外,王教授還注意到清宮有一些尺幅非常巨大的作品,例如「十駿圖」和「十犬圖」。王教授認為,在中國的藝術傳統中,有別於精細的小件作品,如手卷或冊頁,尺幅巨大的作品較不注重寫實,它們更重要的功能是放置在建築空間中的墻壁上,效果近似於壁畫。基於此,王教授認為這些作品形成了一種新的繪畫種類 (genre),即「圖像紀念碑」。在中國的藝術傳統中,早期具有此類功能的藝術類型為石雕,但是石頭會令人聯想到死亡,不適合放置在宮廷中,而製作壁畫的傳統早在晚明時期就已失傳。這些巨大的馬畫巨幅貼落應是被展示在如紫光閣那種巨大的建築空間中,而這些做法在郎世寧義大利東北部老家的馬廳壁畫十分相似;換言之,郎世寧恢復了一項在中國早已失去的壁畫傳統。
最後,王教授分享一幅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掛軸。該畫尺幅巨大,圖中的花園細節非常豐富,最突出的是內繪各種中國本草植物。王教授一一辨認畫中的植物,發現畫中的植物都是夏季的園林花卉,這並不符合中國園林營建中希望一年四季皆有可觀植物的習慣。因此,王教授又考察了當日耶穌會傳教士的往來書信,並比對相關畫冊中描繪的植物種類,發現法國當時的重臣 Henri Bertin (1720-1792) 對中國本草有著濃厚的興趣,並且和北京的傳教士有頻繁的書信往來,是耶穌會的重要贊助人。Henri Bertin 對中國文化有強烈的興趣,曾經想要在法國建一個中式園林,並讓耶穌會傳教士寄送種子和圖樣;據此,王教授認為,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掛軸其實是耶穌會傳教士給贊助人 Bertin 的一件禮物,其中既展示中式花卉的種植方法並附帶種子,又能夠表現北堂當日的禮儀風俗。
王教授的演講內容豐富,在地域和媒材上均有極大跨度,是全球史中西交流領域的重要研究。在會後的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們從不同角度與王教授進行交流,其中討論較熱烈的議題,是時間的合法性,如果時間在帝國的統治合法性中占有重要地位,那麼如何理解天主堂中款式眾多的鐘?對此,王教授回應,不同種類的鐘的目標人群不盡相同,譬如帶著音樂的機械水法鐘就是面向公眾,一些裝飾性較強的鐘則在教堂內展示,屬於異域奇珍的概念,而一些可以在更遠範圍內聽到的鐘,則是試圖與朝廷在報時的合法性場域中進行競爭。除此以外,其他討論的問題還包括樣式雷的作用、當時地產交易的產權和地契問題等。
